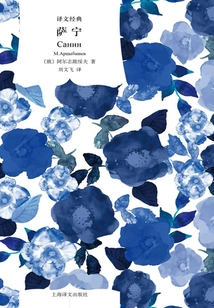
薩寧(譯文經(jīng)典)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阿爾志跋綏夫和他的《薩寧》
(代譯序)
劉文飛
在中學(xué)時(shí)讀魯迅,碰到“阿爾志跋綏夫”這個(gè)佶屈聱牙的姓氏,反復(fù)念了好幾遍,終于記住了這位俄國作家;做研究生時(shí)讀俄國文學(xué)史,幾乎在每一種俄國文學(xué)史中都遇見對(duì)小說《薩寧》的批評(píng)和抨擊,卻一直沒有機(jī)會(huì)直接閱讀阿爾志跋綏夫的這部名作。蘇聯(lián)解體之后,大批遭禁的作家和作品得到“釋放”,阿爾志跋綏夫和他的《薩寧》也終于浮出水面,來到我們面前。
自殺、繪畫和文學(xué)
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阿爾志跋綏夫(Михаил Перт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生于一八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少時(shí)的阿爾志跋綏夫過著恬靜的鄉(xiāng)村生活,在家鄉(xiāng)的學(xué)校里讀了五年書。據(jù)說,他的家鄉(xiāng),哈爾科夫省的阿赫特爾卡(今烏克蘭境內(nèi)),是一座風(fēng)景十分美麗的小城。小城四周是一望無際的草原,靜靜的沃爾斯克拉河從城邊蜿蜒流過,幾乎每一戶人家的屋后都有一個(gè)直抵河邊的花園,對(duì)岸的小山上還有一座靜靜的修道院。也許是受自然美景的熏陶,阿爾志跋綏夫很早就立下當(dāng)一名畫家的志向,后來,阿爾志跋綏夫進(jìn)入哈爾科夫美術(shù)學(xué)校。然而,他在美術(shù)學(xué)校只學(xué)了很短一段時(shí)間,最終也沒能成為畫家,但少時(shí)的志向?qū)λ奈膶W(xué)創(chuàng)作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閱讀阿爾志跋綏夫的作品,我們可以感覺到,優(yōu)美的風(fēng)景描寫是其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而且,作家?guī)缀鯇⑺械娜宋锖褪录挤胖迷谒杂灼鹁褪煜さ纳顖鼍爸校P下的自然就是他故鄉(xiāng)的山水。此外,他從繪畫轉(zhuǎn)向文學(xué),這中間還有一個(gè)偶然的契機(jī),作家本人后來在札記中曾這樣寫道:“童年時(shí)我曾想做一個(gè)獵手,但也不反對(duì)做軍官,后來長時(shí)間幻想做一名畫家,而成為一位作家則是相當(dāng)意外的。這是因?yàn)椋柨品虻囊患覉?bào)紙發(fā)表了我的一個(gè)短篇小說,并付給我八個(gè)盧布,我用這錢買了顏料。后來,我又缺錢,就又寫起了小說,這樣一來,學(xué)畫就讓我感到枯燥,于是我就轉(zhuǎn)向了文學(xué)。”[1]阿爾志跋綏夫?qū)懶≌f的原始動(dòng)機(jī),是為了賺錢去買繪畫的顏料。
在這之前,還有一件不幸的事件對(duì)阿爾志跋綏夫未來的文學(xué)生涯產(chǎn)生了影響。十六歲時(shí),也就是一八九四年春天,由于對(duì)生活感到絕望,阿爾志跋綏夫曾開槍自殺。他傷勢(shì)嚴(yán)重,生命垂危,后奇跡般地活了過來。我們不知道,促使他舉起槍來自殺的那些思想斗爭和矛盾心理是否也是促使他拿起筆來寫作的推動(dòng)力,但自殺前后的強(qiáng)烈感受卻是他久久難以忘懷的。沒等傷愈,他就將那些感覺和體驗(yàn)寫進(jìn)一個(gè)短篇小說,這篇具有“生活素材”和真實(shí)感受的小說不久就順利地在哈爾科夫的《南疆報(bào)》上刊出(《一個(gè)軍官講述的故事》,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后來,自殺事件和自殺者持續(xù)不斷地出現(xiàn)在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中,有人竟說:“很少有哪一篇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沒有關(guān)于死亡及其注定的不可避免性的悲哀思索。在他的長篇和中篇里,死亡幾乎成了主角。”[2]
從畫家到作家,從自殺的體驗(yàn)到文學(xué)的實(shí)踐,阿爾志跋綏夫完成了一次跨越。而畫家的獨(dú)特視角和自殺者的獨(dú)特感受,卻都在他的整個(gè)創(chuàng)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被視為其作家個(gè)性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中最重要的構(gòu)成。
《薩寧》、薩寧和“薩寧性格”
在家鄉(xiāng)小試文筆之后,阿爾志跋綏夫去了彼得堡。一九〇一年,阿爾志跋綏夫在彼得堡的《俄國財(cái)富》雜志上發(fā)表短篇《帕沙·圖曼諾夫》,受到好評(píng),他從此成了一位職業(yè)作家。他連續(xù)發(fā)表小說,在文學(xué)界廣交朋友,還曾嘗試組織一個(gè)旨在反對(duì)“文學(xué)將軍們”的青年作家團(tuán)體,他主持過《教育》雜志的文學(xué)欄,與許多文學(xué)名流進(jìn)行論戰(zhàn),在文壇很是活躍。但是,給他帶來巨大聲譽(yù),使他一時(shí)成為整個(gè)俄國文學(xué)生活之中心的,還是這部長篇小說《薩寧》(Санин)。
《薩寧》寫成于一九〇二年,但是直到一九〇七年才得以發(fā)表在《當(dāng)今世界》雜志的九月號(hào)上。這部需要其編輯用五年時(shí)間來“讀懂”的小說,在社會(huì)上自然也難以獲得一致的評(píng)價(jià),然而,《薩寧》在當(dāng)時(shí)俄國所激起的軒然大波仍是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的,幾乎每份雜志和報(bào)紙都刊登評(píng)論文章,幾乎每位文壇知名人士都公開表態(tài),幾乎每個(gè)百姓都會(huì)在日常談話中提及《薩寧》。有人寫道,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似乎,不是米·阿爾志跋綏夫?qū)懢土怂_寧,而是薩寧寫就了米·阿爾志跋綏夫”[3]。一方面,小說似乎同時(shí)受到兩個(gè)對(duì)立思想陣營的抨擊,激進(jìn)的左派知識(shí)分子認(rèn)為它思想落后,保守的右派人士又認(rèn)為它有傷風(fēng)化;可另一方面,《薩寧》被成千上萬的讀者瘋狂地閱讀,青年學(xué)生們紛紛成立半地下性質(zhì)的“薩寧主義者小組”“自由愛情同盟”之類的組織,小說中的主人公薩寧更是成了眾多青年的仿效對(duì)象,被視為真正的“當(dāng)代英雄”,甚至連當(dāng)時(shí)的黑社會(huì)組織“黑色百人團(tuán)”也將薩寧及其作者樹為自己的旗幟。各種模仿《薩寧》的作品層出不窮,后被批評(píng)界歸納為“阿爾志跋綏夫風(fēng)格”(Арцыбашевшинa),其主要特點(diǎn)就是對(duì)“性問題”的公然關(guān)注,對(duì)社會(huì)的冷漠態(tài)度,以及對(duì)革命性變革前景所持的懷疑目光。正因?yàn)槿绱耍谝徊慷韲骷肄o典中便有了這樣的說法:“《薩寧》在一九〇七年出版后獲得了丟丑的知名度。”[4]
關(guān)于《薩寧》的爭論,其實(shí)都是圍繞其主人公薩寧展開的。小說以主人公的姓氏為題,它從薩寧返回故鄉(xiāng)寫起,到他乘火車離去結(jié)束,寫的是薩寧在家鄉(xiāng)那段時(shí)間的所作所為。他少小離家,其性格是在家庭之外養(yǎng)成的,沒有任何一個(gè)人監(jiān)督過他,沒有任何一只手管教過他,這個(gè)人的靈魂是自由自在地形成的,就像曠野里的一棵樹。他不仇恨任何人,也不為任何人而痛苦;他對(duì)一切都抱著無所謂的態(tài)度;他最常見的神態(tài)就是漫不經(jīng)心的微笑和略帶嘲諷的冷笑;他光明正大地追求享樂,毫不遮掩地袒露心胸。他與農(nóng)夫的孫女一起過夜,月夜在河面的小船上占有了美麗的女教師卡爾薩維娜,甚至對(duì)自己的妹妹麗達(dá)也能生出一陣陣沖動(dòng);他揍了軍官扎魯丁,粉碎了猶太青年索羅維伊契克的信仰,直接導(dǎo)致這兩個(gè)人的自殺;他討厭周圍幾乎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親人,面對(duì)熟人的死亡,他每每無動(dòng)于衷,認(rèn)為“世界上又少了一個(gè)傻瓜”;他身材高大,健壯有力,為所欲為,與此同時(shí),他又很孤獨(dú),很無聊,漂泊不定。這是一個(gè)無政府主義者,一個(gè)個(gè)人主義者,一個(gè)“超人”。魯迅在談到《薩寧》時(shí)說:“這書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無治的(即無政府主義的——引者按)個(gè)人主義或可以說個(gè)人的無治主義。”[5]
關(guān)于這樣一個(gè)形象,眾說紛紜,所謂的“薩寧性格”(Caнинщина)也被提了出來,并成為當(dāng)時(shí)一個(gè)引用頻率極高的詞匯。由于這一形象出現(xiàn)在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后,也就是俄國知識(shí)分子普遍感到失落和沮喪的年代,因此,它就被看成是俄國文化精英之整體“墮落”的象征。激進(jìn)派的文學(xué)家否定《薩寧》,并因薩寧形象所具有的消極意義深感不安。高爾基在《個(gè)人的毀滅》一文中寫道:“如今由精神貧困的人們組成的畫廊被阿志巴綏夫(即阿爾志跋綏夫——引者按)的沙寧(即薩寧——引者按)可恥地完成了。應(yīng)該記住,沙寧已經(jīng)不是市儈意識(shí)企圖給日趨沒落的個(gè)人指出一條生路的第一次嘗試了,在阿志巴綏夫這部作品出現(xiàn)之前,就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勸告:人應(yīng)該用變成走獸的辦法來簡化自己的內(nèi)心生活。”[6]沃羅夫斯基在《巴扎羅夫和薩寧》一文中將這“兩個(gè)虛無主義者”進(jìn)行比較,并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薩寧的特征的總和,意味著對(duì)平民知識(shí)分子半個(gè)世紀(jì)的傳統(tǒng)的背叛,首先是對(duì)為被壓迫階級(jí)服務(wù)的背叛——在社會(huì)生活中,對(duì)義務(wù)的無上命令的背棄——在個(gè)人生活中。”[7]另一位激進(jìn)派批評(píng)家奧爾明斯基說得更直接:“《薩寧》的實(shí)質(zhì)就是用‘伏特加和美女’的口號(hào)去取代‘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的口號(hào)。”[8]
于是,薩寧作為一個(gè)墮落的、“反動(dòng)”的形象,似乎已被永遠(yuǎn)地釘在俄國文學(xué)史的恥辱柱上。然而,在翻譯《薩寧》的過程中,譯者卻也漸漸地讀出了薩寧形象的某些“積極”意義。在二十世紀(jì)之初,濃烈的世紀(jì)末情緒在俄國知識(shí)界彌漫,人們?cè)谑袙暝卺葆逯星笏鳎谑牵鳛橐环N反撥,尼采和叔本華的“自由意志”理論和“超人哲學(xué)”贏得空前共鳴,薩寧的形象就是在這樣的社會(huì)思潮中出現(xiàn)的,因此,這一人物體現(xiàn)出的氣質(zhì)和性格,也是知識(shí)分子步出思想困境的一種選擇,一種方式。另一方面,薩寧身上所體現(xiàn)的個(gè)人主義,其實(shí)也是俄國知識(shí)分子個(gè)性覺醒的一個(gè)新標(biāo)志,超越黨派和集團(tuán)的利益去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與周圍環(huán)境的沖突中捍衛(wèi)自我存在的價(jià)值,這本身就是一種選擇。退一步說,在兩個(gè)陣營尖銳對(duì)立的時(shí)候,像帕斯捷爾納克所言的那種“超越街壘”的方式,未必不是一種明智的立場,更何況時(shí)間后來又證明了,那場街壘戰(zhàn)并沒有帶來很多的積極后果。在小說中不難看出,薩寧雖然不可愛,有時(shí)還很不道德,可他周圍的人,除了幾位女性之外,似乎都還比不上他,扎魯丁和軍官們的愚蠢,尤里的虛偽,梁贊采夫的淺薄,諾維科夫的怯懦……而且,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極端自私的,薩寧至少在真誠和果敢上超過了他們中間的任何一位。當(dāng)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塑造出巴扎羅夫的形象之后,社會(huì)上一片嘩然,當(dāng)時(shí),革命民主派批評(píng)家曾出面肯定巴扎羅夫形象的進(jìn)步意義,認(rèn)為在巴扎羅夫的“虛無主義”中包含著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不滿,對(duì)變革的渴望;五十年之后,自由派批評(píng)家又幾乎采用與革命民主派批評(píng)家同樣的方式,在將薩寧與巴扎羅夫做了一番比較之后,認(rèn)為薩寧形象的塑造是一個(gè)“新的發(fā)現(xiàn)”,由此,關(guān)于薩寧是“二十世紀(jì)的巴扎羅夫”的說法就流傳開來。薩寧和十九世紀(jì)俄國文學(xué)中的“多余人”形象一樣,既是一種苦悶、失落,乃至墮落的象征,同時(shí)也體現(xiàn)著某種抗議,蘊(yùn)涵著某種積極意義。
樂觀的悲劇
除《薩寧》外,阿爾志跋綏夫的重要作品還有《帕沙·圖曼諾夫》(一九〇一)、《旗手戈洛洛波夫》(一九〇二)、《蘭德之死》(一九〇四)、《人浪》(一九〇七)、《工人施維廖夫》(一九〇九)、《絕境》(一九一〇)等,他還寫有多部劇本,此外,他從一九一一年起在報(bào)刊上發(fā)表隨筆性文字《作家札記》,持續(xù)不斷地一直寫到逝世,最后積累成厚厚幾大卷。
將阿爾志跋綏夫的創(chuàng)作當(dāng)成一個(gè)整體來觀察,可以在其中發(fā)現(xiàn)一個(gè)巨大的矛盾。一方面,無政府主義和個(gè)人主義作為作家世界觀中的重要構(gòu)成,在阿爾志跋綏夫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著深刻的滲透,其作品中的人物張揚(yáng)個(gè)性,追求個(gè)性的自由和個(gè)人欲望的充分滿足,他們的活動(dòng)營造出一個(gè)享樂主義的歡樂場景;另一方面,一種濃重的悲觀氛圍又始終籠罩在阿爾志跋綏夫的作品中,他的主人公們要么像工人施維廖夫那樣時(shí)刻處在被圍捕的恐懼之中,要么像《薩寧》中的尤里那樣感到絕望,就連薩寧自己,也同樣不時(shí)地感到無聊。《薩寧》中的人物一個(gè)接一個(gè)地死去,僅自殺者就有扎魯丁、尤里、索羅維伊契克三人,而起過自殺念頭的人就更多了,謝苗諾夫、麗達(dá)、柳麗婭……在另一部長篇《絕境》中,阿爾志跋綏夫更是一口氣寫了七個(gè)主人公的自殺!他的作品,幾乎成了一個(gè)“自殺者俱樂部”。悲觀與樂觀,歡樂和絕望,這兩種對(duì)立的因素在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中構(gòu)成一個(gè)奇異的統(tǒng)一體。阿爾志跋綏夫在一套文集的序言中這樣寫道:“當(dāng)然,死神那陰暗、恐怖的身影自然也貫穿了他的整個(gè)創(chuàng)作——這創(chuàng)作時(shí)而是節(jié)日般明朗的,陽光燦爛的,時(shí)而又是沉重憂愁的,毫無出路的。與此相關(guān),他同時(shí)代的批評(píng)家們的意見也分為兩類:一些人驚嘆他是一個(gè)崇拜太陽的作家,一位愛情和永恒歡樂的歌手;另一些人則認(rèn)為他屬于報(bào)喪者和掘墓人,是不道德的死亡傳道者,是人類道德的毀滅者。”[9]蘇聯(lián)早期有一部劇作名叫“樂觀的悲劇”,或許,我們也可以用這個(gè)題目來概括阿爾志跋綏夫的整個(gè)創(chuàng)作。
我們可以認(rèn)為,將兩種因素串聯(lián)起來的是這樣一個(gè)通俗的邏輯:人注定要死,因而要及時(shí)行樂,正所謂“人生幾何,對(duì)酒當(dāng)歌”。然而,我們更應(yīng)該從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和阿爾志跋綏夫本人的個(gè)性這兩個(gè)方面來考察這種“悖論組合”的原因。
阿爾志跋綏夫所處的時(shí)代,是俄國知識(shí)分子空前彷徨的時(shí)代,“到民間去”的運(yùn)動(dòng)無果而終,國家的專制統(tǒng)治讓人窒息,濃重的世紀(jì)末情緒還未散去,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又使許多人“向右轉(zhuǎn)”,后來,就是殘酷的世界大戰(zhàn)和動(dòng)蕩的十月革命。這樣的社會(huì)和時(shí)代背景,直接導(dǎo)致那一時(shí)期許多作家創(chuàng)作中悲觀成分的加重。對(duì)阿爾志跋綏夫的“頹廢傾向”持激烈的批判態(tài)度并因自己樂觀浪漫的風(fēng)格而被視為阿爾志跋綏夫之對(duì)立面的高爾基,就和阿爾志跋綏夫一樣也曾嘗試過自殺;認(rèn)為阿爾志跋綏夫“非常有天賦”卻因他“將惡帶給了許多人”[10]而感到憤怒的托爾斯泰,最終自己也在絕望中“出走”。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失望,使人們更關(guān)注自我,同時(shí),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也極易產(chǎn)生并成氣候,它們?cè)谖膶W(xué)中的反映,往往就是阿爾志跋綏夫式的挑逗和褻瀆。這種由內(nèi)心真誠引發(fā)的玩世不恭,在絕望中生成的嬉笑,被細(xì)心的俄國大詩人安年斯基準(zhǔn)確地定義為“感傷主義的漫畫”[11]。
像在每一位作家那里的情形一樣,阿爾志跋綏夫的作品風(fēng)格,包括他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他的個(gè)性和遭遇。阿爾志跋綏夫三歲時(shí),在縣警察局當(dāng)過局長的父親就去世了,卻將結(jié)核病作為“遺產(chǎn)”留給了他,原籍波蘭的母親獨(dú)自帶大阿爾志跋綏夫。未遂的自殺使阿爾志跋綏夫終身受病痛折磨,他很早就耳聾,后來又幾乎失明。這一切使他養(yǎng)成一種既敏感又封閉、既膽怯又無羈的個(gè)性,在文學(xué)界,他以好斗和無禮著稱,而這反過來又惡化了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在《薩寧》發(fā)表前后,他數(shù)次被居住地的政府機(jī)關(guān)驅(qū)逐(如一九〇一年被逐出彼得堡,一九〇八年被逐出雅爾塔和塞瓦斯托波爾)。由于《薩寧》中的“瀆神”言論,俄國主教甚至要將他革出教門,對(duì)他發(fā)出詛咒;而《薩寧》造成的“風(fēng)化”問題,使阿爾志跋綏夫多次面臨吃官司的危險(xiǎn);一九二三年,由于不堪言論和人身的不自由,阿爾志跋綏夫離開莫斯科,流亡到母親的祖國波蘭,四年之后,他于貧病交加之中在華沙去世。作家的生活經(jīng)歷對(duì)作家個(gè)性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而作家的個(gè)性無疑又會(huì)影響到作家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在一篇文章中,阿爾志跋綏夫?qū)⒆约簞?chuàng)作中的“矛盾”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因?yàn)樗冀K認(rèn)為,“世界上沒有絕對(duì)的真理”,因此,“重要的東西,并不是作家描寫的那些東西,并不是他似乎揭示出的那些各種各樣的真理,而是他本人的個(gè)性,因?yàn)閭€(gè)性是偉大而又獨(dú)特的”(《契訶夫之死》,一九〇七)。在阿爾志跋綏夫“樂觀的悲劇”中,我們仿佛窺見了作家的個(gè)性及其演變過程。
總之,優(yōu)美、燦爛的景色描寫和細(xì)膩、陰暗的心理描寫相互交替,極端的個(gè)人主義哲學(xué)和俄國文學(xué)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責(zé)任感此起彼伏,歡樂的感官享樂態(tài)度和對(duì)整個(gè)存在的深刻懷疑精神處處對(duì)峙,這一切共同組合成了阿爾志跋綏夫小說的整體風(fēng)貌。
魯迅和阿爾志跋綏夫
第一個(gè)將阿爾志跋綏夫及其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人,就是魯迅,“阿爾志跋綏夫”這個(gè)拗口的譯名也正是魯迅先生的首創(chuàng)。在同時(shí)代的外國文學(xué)中,魯迅最看重俄國文學(xué),認(rèn)為在其中可以看見“被壓迫者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而在同時(shí)代的俄國作家中,魯迅似乎又是非常偏愛阿爾志跋綏夫的。一九二〇年,魯迅從德文轉(zhuǎn)譯了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即《工人施維廖夫》),譯文在《小說月報(bào)》一九二一年第七至十二期上連載,后又出單行本,該單行本的出版時(shí)間甚至還早于魯迅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在《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后》一文中,魯迅對(duì)阿爾志跋綏夫這篇小說做了這樣的歸納:“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義,改革者為了許多不幸者們,‘將一生最寶貴的去做犧牲’,‘為了共同事業(yè)跑到死里去’,只剩下一個(gè)綏惠略夫了。而綏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躡里,包圍過來的便是滅亡;這苦楚,不但與幸福者不相通,便是與所謂‘不幸者們’也全不相通,他們反幫了追躡者來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另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地糟蹋生活’。”[12]《工人綏惠略夫》寫于一九〇八年,寫在《薩寧》發(fā)表之后,講的是一位在革命失敗后遭到追捕的工人革命者,在逃亡途中四處遭遇冷漠,甚至被他立志為之獻(xiàn)身的民眾所出賣,最后,在劇院中被抓到的他,絕望地舉槍向觀眾胡亂射擊。為民眾斗爭的人卻得不到民眾的理解和支持,魯迅在這里看到了問題的所在,看到了“改造國民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許正是這一點(diǎn),促使魯迅動(dòng)手翻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不過,使阿爾志跋綏夫如此迅速地來到中國的,還有一個(gè)偶然的原因,魯迅自己后來在一九二六年談到這段“有點(diǎn)有趣的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shí),中國也對(duì)德宣了戰(zhàn),戰(zhàn)后“自然也要分得戰(zhàn)利品”,那便是上海德國商人俱樂部中的德文書,教育部派人去整理這些書,魯迅也是其中的整理者之一,他在那些書中發(fā)現(xiàn)了一本德文版的《工人綏惠略夫》,愛不釋手地讀過之后,便翻譯起來。魯迅自己調(diào)侃道:“‘對(duì)德宣戰(zhàn)’的結(jié)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里的‘公理戰(zhàn)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13]
在《工人綏惠略夫》之后,魯迅還翻譯了阿爾志跋綏夫的三篇作品,分別是短篇小說《幸福》和《醫(yī)生》,以及散文《巴什庚之死》。《幸福》寫一個(gè)丑陋的妓女為了獲得幾個(gè)盧布,甘愿脫光衣服在雪地中忍受一個(gè)變態(tài)者的棍擊,當(dāng)她遍體鱗傷地走近夜茶館,想到了“吃,暖,安心和燒酒”,內(nèi)心便“已經(jīng)充滿了幸福的感情”。《醫(yī)生》寫一個(gè)猶太醫(yī)生經(jīng)過激烈的思想斗爭終于違背醫(yī)生的天職,拒絕搶救那個(gè)迫害過猶太人的警察廳長。《巴什庚之死》是一篇悼念文章,魯迅是從日文轉(zhuǎn)譯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巴什庚(通譯巴什金)是阿爾志跋綏夫的好友,他倆不僅文學(xué)趣味相投,還是同病相憐的患難兄弟——都一直飽受肺病的折磨。巴什金的死亡使阿爾志跋綏夫既體驗(yàn)了深切的哀痛,也感覺到了死神的迫近,在那篇散文中,他的這些體驗(yàn)構(gòu)成一段感人的傾訴。
在魯迅所涉及的外國作家中,他翻譯作品數(shù)量最多的,他評(píng)論頻率最高的,當(dāng)首推阿爾志跋綏夫。這首先是由于,阿爾志跋綏夫作品的內(nèi)容符合魯迅當(dāng)時(shí)的“口味”,寫主人公與環(huán)境的對(duì)立,寫主人公近乎絕望的抗?fàn)帲@也是魯迅本人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其次,從個(gè)性和文風(fēng)上看,魯迅和阿爾志跋綏夫也有相近之處,他倆的為人和作文都個(gè)性極強(qiáng),愛憎分明,敢說敢做,主張不妥協(xié)的戰(zhàn)斗精神,乃至復(fù)仇。兩人的語言也都清麗,冷峻,有入木三分的力度,屬于魯迅先生自己所言的“激憤”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魯迅后期對(duì)阿爾志跋綏夫的評(píng)價(jià)有所改變,曾舉《薩寧》為“淫蕩文學(xué)盛行”的例子(《二心集〈藝術(shù)論〉譯本序》,一九三〇),并在阿爾志跋綏夫的作品里“看見了絕望和荒唐”(《南腔北調(diào)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一九三二)。
正是由于魯迅的推崇和譯介,阿爾志跋綏夫較早地受到了中國讀者的關(guān)注和喜愛。在魯迅的翻譯之后,阿爾志跋綏夫的《巴莎·杜麥拿大》(即《帕沙·圖曼諾夫》)、《血痕》、《朝影》、《寧娜》、《夜》、《戰(zhàn)爭》等作品,都相繼被譯成中文。一九三〇年,他最重要的作品《薩寧》幾乎同時(shí)在中國出版了三個(gè)譯本,譯者分別是鄭振鐸、潘訓(xùn)和伍光訓(xùn),在中國也掀起了一股“薩寧熱”。不過,這幾個(gè)譯本都是從英文轉(zhuǎn)譯的。
這個(gè)譯本根據(jù)俄文版《阿爾志跋綏夫三卷集》(莫斯科,TERRA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一卷譯出。為便于讀者閱讀,譯者特將一份《主要人物表》列于書前。譯文中的錯(cuò)誤之處,希望得到讀者和同行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