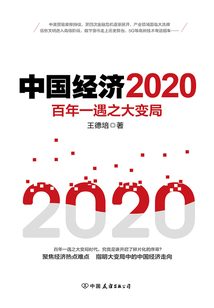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經濟學:算命 預測 腦洞?——社會需要第一性原理
經濟學“科學中毒、量化成風”,走火入魔,竟將人的面相也與業績掛鉤進行量化分析。頂尖雜志《經濟學人》曾刊登一篇文章,研究的是基金經理面部寬高比對業績的影響,得出的結論是基金經理的臉越大,業績越差。“大臉貓”們震驚之余,紛紛表示“躺著也中槍”,網友調侃《經濟學人》成了《神學人》。本以為這只是一次嚴謹的玩笑,誰承想,沿著這個套路,竟又有了新的“研究成果”。《行長的面部寬高比影響銀行績效的路徑研究》——南開大學和天津外國語大學的學者研究發現,銀行行長面部寬高比通過體現出的權力感影響銀行內部績效;高面部寬高比的分析師,預測準確度更高——西南財大、上海財大、南洋理工的學者合作論文被頂級會計期刊JAR接受;更有《窄臉當道,寬臉當家》一文紅爆網絡,該文聲稱窄臉在全世界都更受歡迎,甚至憑借畫作就得出結論:就連悲憫的耶穌都是巴掌臉,而寬臉的人則被形容為攻擊性、統治力都更強,并因此得以掌控世界,例子竟幾乎都是影視化的文學形象。從論點到論據,無一不令人瞠目結舌、哭笑不得。本屬科學的經濟學,為何一夜之間竟異化成了算命、相面的行當?
直觀來看,人類本身就是一種感性與理性并存的生物。感性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生物及機器的最大不同之處,感性也鑄成了人的性格與行為的多變與不確定性。然而,刻意忽視人類思維方式中的非理性成分,將人的外貌與成績全盤量化、強行掛鉤,并以此分析人類的做法,毫無疑問是“為了科學而科學”,內里卻是“算命”一般的套路。殊不知“前半生風波坎坷,后半生飛黃騰達”的算命公式,恰恰是“順毛摸”式的主觀臆斷、信口開河。誠然,科學需要量化分析,然而科學與量化之間從來不能簡單地畫上等號。若經濟學僅需相面就可以預測,那么通過固定的面相模板篩選從業人員,是否就能夠規避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了呢?忽略資本原罪(逐利性)與政府原罪(超發貨幣)而將責任歸咎于命理學、面相學,強行將科學“迷信化”,無疑是荒謬的。具體到中國,曾幾何時,多少在A股封神的“股神”們,趁著特殊國情的東風扶搖直上,卻熱衷于披上科學的外衣,信誓旦旦地為其股市神話構建一整套“科學體系”以贏得“韭菜”們擁躉。但最終,所謂的“股市科學”卻如大廈轟然倒下,“大神”們被撕下畫皮現了原形,徒留雞毛滿地。如今,更是連經濟學家都“下海”做起了神棍,也就難怪英國“神劇”《是,大臣》中諷刺經濟學家“恐怕他更不可能懂經濟”了。
現代經濟學雖脫胎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但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其核心即是研究工業經濟時代人們生產生活中的經濟規律。殊不知,任何經驗、知識一旦落紙成文,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天然的滯后性。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已經從工業文明快步進入信息文明乃至更新的時代,然而不僅經濟學,當前諸多學科的邏輯與理論卻仍然停留在工業經濟時代,滯后的理論難以對當下做出解釋與預判,以致陰謀、陽謀、道德甚至算命等諸多論調甚囂塵上。披著科學、政治、人性的外衣,“腦洞”一個賽一個的大,語不驚人死不休,今天“馬云實際上是發國難財”,明天“特朗普內閣全員‘通共’”,后天“某某明星又如何如何”。只是苦了“吃瓜群眾”,今天看這個,明天看那個,甲說“貿易戰中國贏了”似乎有理有據,乙說“美國還有后招不可輕敵”似乎也很有道理,缺乏自身觀點與判斷的人,最終要么徹底淪為某一論調、某一作者的信徒,要么在爆炸式的信息與觀點中惶惶度日。
究其根本,當前正處于時代和社會的大拐點時期,世界前所未有地復雜混亂。從世界范圍看,國家、企業、資本、科技四大象限攪得天翻地覆。一方面,第四次金融危機正式展開,中美貿易摩擦持續,世界經濟普遍陷入低迷,疊加債務危機、難民問題,再加上特朗普這位“朝三暮四”、到處惹禍的美國總統,全世界的國家都沒了方向;另一方面,科技發展日新月異,AI(人工智能)取代人工、生命科學的“上帝之手”等都成為正在進行時,底層人民的被剝奪感日漸加重,不安全,很慌張。從國內社會看,改革開放40多年,發展成果斐然,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主要矛盾也已經轉化,但中國的發展具有非典型性,時代、互聯網、地域、貧富等因素切割出太多群體。從耄耋老人、“失落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再到身為互聯網原住民的新生代青少年,其中的代溝有如天塹,更不必說群體內部也是千差萬別。一線城市高企的房價是趕上順風車的“70后”、“80后”“平步青云”成為千萬富翁的助力,卻被“90后”、“00后”視為“豺狼猛虎”,就連在北上廣深“蝸居”都成為遙不可及的奢望。再加上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平臺顛覆了信息的單向線性傳播,變為網格式甚至病毒式傳播,渲染不安,營銷焦慮。大拐點時期內外急劇變化,社會經歷系統性的震蕩,人們愈發看不懂形勢,由此帶來內心的不安全感也在所難免。人們急需一套方法和理論加以收斂安定,對現實做出合理解釋。
事實上,越是拐點時期,越要穿透復雜混沌的表象,擺脫認知歸因偏差,回歸事物本質去探索其中的真實聯系,社會迫切需要第一性原理。第一性原理本義是一個計算物理或計算化學專業名詞,通俗地講,即破解復雜、回歸本質,對一系列現象與問題進行收斂。打破知識藩籬,回歸事物本質,去思考最基礎的要素,從事物本源出發尋求突破口,才能快速、直接地尋找到答案,不致落入窠臼。另一方面,第一性原理也促使人類疾速創新,帶來科技革命。
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就對第一性原理思考法極為推崇:“通過第一性原理,我把事情升華到最根本的真理,然后從最核心處開始推理。”第一性原理可以說是馬斯克在網絡支付、電動汽車、航天運輸、新能源應用等諸多領域取得顛覆式創新的方法論源泉。另一方面,第一性原理的本質導向性在學科理論創新中顛覆了原有的認知,帶來了認知革命。地緣政治學先驅麥金德以地緣為國際關系的核心本質,從空間革命的角度考察地理對人類歷史的影響,開啟“麥金德時代”,其基本理論范式在1900年后的人類歷史中一次次被印證;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更是洞穿人類文明更迭的本質,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神預言”特朗普將成美國總統;在物理學領域,人類對世界本質的探索腳步從未停歇,從分子到原子,從原子到量子,再到暗物質,每一個“微乎其微”的發現都掀起科學狂潮;生物學界對膽固醇、垃圾基因等的刻板印象,也在一次次尋根溯源的認知探索中逐漸改變。
當科技革命與認知革命齊發,原本工業文明的規律與邏輯下的許多學科基礎面臨被釜底抽薪的局面,現有的學科壁壘將被打破,迎來跨學科的交融發展時代。經濟學也許將掙脫“經濟活動規律”的桎梏,與心理學、人類學、倫理學、歷史學等領域相互交融,洞穿人性或將成為經濟學的重要分支。畢竟,在未來的體驗經濟時代中,“人”作為體驗的主體,將成為時代主題詞,破解人性的復雜也將成為體驗經濟時代的關鍵。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披上科學的外衣玩迷信的一套。相反,以第一性原理洞穿事物本質,是一種科學理性的思維,可幫助人們坦然面對大拐點,迎接大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