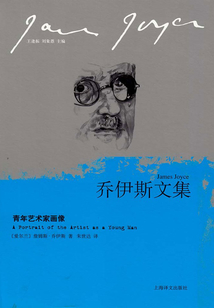
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喬伊斯文集)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序
藝術(shù)家的心靈歷程
愛(ài)爾蘭著名作家詹姆斯·喬伊斯1904年在都柏林開(kāi)始創(chuàng)作長(zhǎng)篇小說(shuō)《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1914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歷時(shí)10年。他于1904年1月7日,在他母親逝世之后4個(gè)月起意寫一個(gè)自我畫像。在都柏林剛籌建的雜志《達(dá)那》編輯們的慫恿之下,他在妹妹梅布爾的筆記本里急就了一篇敘述性的散文,題為《藝術(shù)家畫像》。在這篇散文作品中,喬伊斯采用了他原先寫成的所謂的“穎悟性速寫”(epiphany),大致勾勒了一個(gè)故事,并聲言要在散文中用“流動(dòng)的現(xiàn)在時(shí)”表述過(guò)去,以充分體現(xiàn)“情感的跌宕”。
他將書稿寄給《達(dá)那》雜志,遭拒絕。不久,他便開(kāi)始重寫一部自然主義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題為《斯蒂芬英雄》。喬伊斯是在1904年2月2日22歲生日那天開(kāi)始寫作《斯蒂芬英雄》的。他想以此向《達(dá)那》雜志編輯們表明,“在描寫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有一個(gè)比他們漫無(wú)目的的討論更有興趣的題材”。他對(duì)弟弟斯坦尼斯拉斯·喬伊斯說(shuō),這部小說(shuō)將是自傳性的,諷喻性的。在小說(shuō)中,喬伊斯描寫了許多熟識(shí)的朋友和天主教耶穌會(huì)修士。書名《斯蒂芬英雄》本身就含有諷刺的意義。1904年4月,他完成了11章,一年多以后,他寫到25章時(shí)(差不多是他計(jì)劃創(chuàng)作的一半),感到文思枯竭,轉(zhuǎn)而寫作《都柏林人》和準(zhǔn)備《室內(nèi)樂(lè)》的出版事宜。現(xiàn)在在哈佛大學(xué)圖書館保存的手稿始于16章中間部分而在第26章中間部分戛然中止。在《斯蒂芬英雄》中,喬伊斯對(duì)他的技巧“穎悟性速寫”作了一個(gè)界定,認(rèn)為它是一種“無(wú)論是在語(yǔ)言或是在手勢(shì)的粗俗性中還是在心靈本身一個(gè)值得銘記的閃念中突發(fā)性的精神的表現(xiàn)”。文藝評(píng)論家西奧多·斯潘塞認(rèn)為,與其說(shuō)喬伊斯的穎悟性的速寫是戲劇性的,還不如說(shuō)是抒情性的,這與作品主人公關(guān)于文學(xué)形式的觀點(diǎn)是一致的。哈佛大學(xué)教授哈利·列文認(rèn)為,喬伊斯運(yùn)用令人頭暈?zāi)垦5霓D(zhuǎn)換場(chǎng)景和思維的流動(dòng)的手法實(shí)質(zhì)上是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宗教式啟示的替代物。
1904年,喬伊斯出國(guó)遠(yuǎn)游巴黎、蘇黎世和的里雅斯特等地。在這期間,他將《斯蒂芬英雄》改寫為《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在《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中保留了許多前者的人物和事件。《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自1914年2月至1915年9月在倫敦《利己主義者》雜志上連載,1916年在紐約首次出版。
意象派詩(shī)歌創(chuàng)始人埃茲拉·龐德在1915年9月讀了《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之后給詹姆斯·喬伊斯寫信說(shuō):“我認(rèn)為這本書與福樓拜、司湯達(dá)的作品一樣具有一種永恒的價(jià)值。”他認(rèn)為,喬伊斯的文體清澈而簡(jiǎn)約,沒(méi)有堆砌無(wú)用的詞匯和句子。在另一篇發(fā)表在《利己主義者》雜志1917年2月號(hào)的文章中,他指出,喬伊斯的小說(shuō)將永遠(yuǎn)成為英語(yǔ)文學(xué)的一部分。他說(shuō),他不可能就喬伊斯和任何英國(guó)或愛(ài)爾蘭作家做一比較,因?yàn)樗c其他的英國(guó)或愛(ài)爾蘭作家太不同了。
雖然H·G·威爾士并不贊同喬伊斯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的試驗(yàn),但他還是認(rèn)為《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將與《格列佛游記》一樣成為文學(xué)的一大成就。他說(shuō),和世界上其他最好的文學(xué)作品一樣,這是一部教育的小說(shuō);它是迄今為止所有作品中最生動(dòng)、最令人信服地描述了愛(ài)爾蘭天主教家庭孩子成長(zhǎng)的故事的小說(shuō)。
一
喬伊斯在《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扉頁(yè)引用了古羅馬詩(shī)人奧維德《變形記》里的話:Et ignotas animum dimittit in artes(用心靈以使藝術(shù)黯然失色)。在這里,喬伊斯試圖用新柏拉圖主義的理念,創(chuàng)造一顆超越藝術(shù)的藝術(shù)家靈魂。青年藝術(shù)家斯蒂芬·德達(dá)羅斯采用了希臘發(fā)明之神德達(dá)羅斯的名字。斯蒂芬在成長(zhǎng)的青春歲月與愛(ài)爾蘭祖國(guó)、家庭、天主教傳統(tǒng)始終處于格格不入的境地。德達(dá)羅斯的兒子伊卡洛斯乘上他父親發(fā)明的一對(duì)翅膀,因飛得離太陽(yáng)太近而墜落。這是斯蒂芬生來(lái)就要為之服務(wù)的目的的一種預(yù)言,這是藝術(shù)家在他的工作室里用大地的沒(méi)有生命的東西制造出一個(gè)新的生命的象征。他的飛翔是他的起點(diǎn),終以墜落而告終。斯蒂芬終因“不想再侍候上帝”而走上自我流放的道路。他決心沖出民族、語(yǔ)言、宗教的牢籠。小說(shuō)本身賦有一種戲劇性的悲劇色彩。希臘神德達(dá)羅斯之所以想全心致力于藝術(shù),根據(jù)奧維德的解釋,他是希冀躲開(kāi)大地和海洋的統(tǒng)治者,是因?yàn)椋?
…longumque perosus
exsilium,tractusque soli natalis amore…
(在太漫長(zhǎng)的流放中
德達(dá)羅斯思念故土)
藝術(shù)家的自我流放和對(duì)精神家園的思念更增加了這種喬伊斯式的悲劇效果。喬伊斯式的悲劇風(fēng)格每每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為生與死所困擾,而斯蒂芬則在嚴(yán)峻的天主教教規(guī)與世俗的享樂(lè)和藝術(shù)之間猶豫不決。他最終呼道:
老父,你這老巧匠給我以幫助吧。
這一吁請(qǐng)讓人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呼吁:“父啊,你為什么這般遺棄我!”
伊卡洛斯的墜落(fall)在《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中幾乎具有一種預(yù)言的威力。fall既預(yù)示亞當(dāng)夏娃的墜落,又預(yù)示不想再侍候上帝的早晨之星路濟(jì)弗爾墮落成撒旦——天使的墮落;既預(yù)示伊卡洛斯的墮落,又預(yù)言斯蒂芬的墮落和對(duì)天主教的反叛,也預(yù)言雪萊的“形單影只,成年漂泊”和納什的“光明從空中墜落”。“星星隕滅了,細(xì)膩的星塵塵埃在宇宙間掉墜下來(lái)。”這《舊約·以賽亞書》中的fall的形象貫穿在《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之中。
另一貫穿整部小說(shuō)的形象便是metamorphoses(變形)。從斯蒂芬到伊卡洛斯,從路濟(jì)弗爾到撒旦,從象牙塔到E—C到海鳥姑娘,從E—C到貧民區(qū)妓女的變形,其主調(diào)都是墮落。
喬伊斯在fall和metamorphoses之間描寫了一個(gè)從小經(jīng)受天主教傳統(tǒng)教育、在冷峻的天主教耶穌會(huì)修士們布道中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青年的心靈歷程。《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是一部藝術(shù)小說(shuō)(Kunstlerroman),又是一部教育小說(shuō)(Bildungsroman)。它和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勃特勒的《眾生之路》、吉辛的《新格魯勃街》、托馬斯·哈代的《心愛(ài)的》、德萊塞的《天才》、諾里斯的《范多弗與獸性》、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xué)習(xí)時(shí)代》、司湯達(dá)的《亨利·勃呂拉傳》一樣,是描寫青年、描寫藝術(shù)家成長(zhǎng)的小說(shuō)。在小說(shuō)中,多愁善感的、內(nèi)向的、以個(gè)人為中心的藝術(shù)家是主角,是堂吉訶德式的英雄。藝術(shù)家青春時(shí)期的憂郁、感傷、困惑和感悟便是小說(shuō)的主題。斯蒂芬關(guān)注的是純美學(xué)和阿奎那的論述。他的心靈在與都柏林社會(huì)、天主教、式微的家庭的沖突中成熟起來(lái)。可以這么說(shuō),這部關(guān)于藝術(shù)家成長(zhǎng)故事的藝術(shù)小說(shuō)就是一部描述宗教與世俗、自我抑制與激情、肉欲與理智、藝術(shù)與生活沖突的作品。喬伊斯在這部小說(shuō)中描寫的不是“一位藝術(shù)家”,而是帶有定冠詞的“藝術(shù)家”,正如W·Y·廷達(dá)爾所指出的,這表明喬伊斯描寫的是一個(gè)特別的、也許含有諷刺含義的一類人的畫像。這個(gè)藝術(shù)家就是斯蒂芬英雄類的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一個(gè)人。斯蒂芬意味著殉道者、巧匠、流放者、希伯來(lái)、基督教、希臘和傲慢的罪人。
二
無(wú)論斯蒂芬在家時(shí),還是在克朗哥斯公學(xué)、貝爾維迪爾公學(xué)或在都柏林大學(xué)學(xué)院,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時(shí)而明確時(shí)而朦朧地尋覓真正的自我,尋覓自己的歸屬。斯蒂芬摒棄了污穢的、愚蠢的、爾虞我詐的環(huán)境,飛越出式微的家庭、虛榮的父親、呆板信教的母親、“吞食自己生養(yǎng)的小豬的”民族、嚴(yán)峻的冷漠的天主教教會(huì)的網(wǎng)去尋找自我的。斯蒂芬懷疑自己與父母、兄弟姐妹的關(guān)系是一種神秘的領(lǐng)養(yǎng)的關(guān)系,而不是一種血緣的關(guān)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兄弟姐妹的確切數(shù)字。
他是一個(gè)學(xué)究式的、自戀的唯我主義者,一個(gè)以自我為中心的叛逆者。他與都柏林周圍的環(huán)境格格不入,有一種彌漫整個(gè)身心的孤獨(dú)感。孤獨(dú)感正是敏感的藝術(shù)家的顯著特征之一。喬伊斯在小說(shuō)開(kāi)首就寫道:
從前,在一個(gè)很美妙的時(shí)刻,有一頭哞哞母牛在路上踽踽而行,這頭哞哞母牛在路上彳亍而行時(shí)遇見(jiàn)了一個(gè)名叫小杜鵑的可愛(ài)的小孩兒。
斯蒂芬一降生就生活在異類的環(huán)境里。小杜鵑這稱呼,對(duì)斯蒂芬來(lái)說(shuō)是再適合不過(guò)的了。雌杜鵑每每將蛋下在別類鳥的巢里。這注定了斯蒂芬作為藝術(shù)家的孤獨(dú)的人生。
斯蒂芬在克朗哥斯公學(xué)遭受教導(dǎo)主任多蘭神父的鞭笞是藝術(shù)家的自我第一次與權(quán)威發(fā)生了沖突。他打碎了眼鏡,阿納爾神父允許他可以不用讀書,而多蘭神父卻誣蔑他為“懶惰的小騙子”。這是不公正而殘酷的。藝術(shù)家要去跟院長(zhǎng)說(shuō),他被錯(cuò)誤地體罰了。他想,像這樣告發(fā)冤枉的事在歷史上有人干過(guò),那是偉人。他于是飯后散步時(shí)不是踅向走廊,而是爬上右邊通向城堡的樓梯,鼓足了勇氣去找教區(qū)長(zhǎng)。于是,藝術(shù)家成了偉人,成了喬伊斯式的孤獨(dú)的英雄。他認(rèn)為,他的命運(yùn)是要躲避任何社會(huì)性的或宗教性的派別。他注定要與眾不同地領(lǐng)會(huì)他自己的智慧,或者在世界的各種陷阱中周旋,自己來(lái)領(lǐng)會(huì)別人的智慧。
甚至當(dāng)他16歲躺在妓女的懷中,他仍然是孤傲的,緊緊抓住他的自我不放。在喬伊斯的自然主義的描述中給人一種疏離感,在男女的接觸中似乎有一種巨大的不可逾越的藩籬橫亙?cè)谒麄冎g。
他默默地呆立在房間中央,她走上前來(lái)快活地正經(jīng)八百地一把抱住他。她那滾圓的手臂將他摟在懷里,他一見(jiàn)她的正經(jīng)而嫻靜的臉龐貼向他,一感覺(jué)到她溫?zé)岬娜榉科届o地在身上摩挲,他遽然歇斯底里地嚶泣起來(lái)。愉悅和釋然的眼淚在他的快樂(lè)的眼睛里閃爍,他張開(kāi)了嘴唇,但并不想說(shuō)話。
她用她那丁零當(dāng)啷的手撫摸他的頭發(fā),叫他小無(wú)賴。
吻我,她說(shuō)。
他不愿躬身去吻她。他只想緊緊地偎在她的懷中,被輕輕地、輕輕地、輕輕地?fù)崮ΑT谒膽驯е兴蝗蛔兊脧?qiáng)大、無(wú)畏而充滿自信。但他不愿躬下身子去吻她。
她霍地一伸手將他的頭壓下來(lái),她的嘴唇與他的嘴唇緊緊貼在了一起,從她那畢露的抬起的眼睛里他穎悟到她所有動(dòng)作的含意。這對(duì)于他太過(guò)分了。
桀驁不馴的藝術(shù)家孤獨(dú)的自我的另一面就是異端。他所信奉的思想與世俗迥異。他崇尚的是浪漫主義詩(shī)人拜倫,認(rèn)為丁尼生只是一位韻律家,而最偉大的詩(shī)人是拜倫。但在都柏林庸俗的“有教養(yǎng)的”中產(chǎn)階級(jí)看來(lái),拜倫純粹是個(gè)異端,“一個(gè)不道德的人”。斯蒂芬第一次因?yàn)閳?jiān)信自己的異端思想而挨了一頓揍。即使斯蒂芬雙手被反綁在身后,同學(xué)從溝里操起一根長(zhǎng)長(zhǎng)的白菜幫子扔在他身上,用手杖猛揍他的腿,赫倫嚴(yán)詞要求他承認(rèn)拜倫不好,藝術(shù)家仍然是一個(gè)斷然的“不”。
由于與周圍環(huán)境格格不入,斯蒂芬在同學(xué)的眼中無(wú)異于一個(gè)“魔鬼”。同學(xué)達(dá)文對(duì)斯蒂芬說(shuō):“你真是一個(gè)可怕的人,總是孤獨(dú)一個(gè)人。你完全脫離了愛(ài)爾蘭民族主義運(yùn)動(dòng)。你是一個(gè)生來(lái)就對(duì)一切冷嘲熱諷的人。”但藝術(shù)家卻認(rèn)為,“這個(gè)民族、這個(gè)國(guó)家、這人生創(chuàng)造了我,我只是說(shuō)出了一個(gè)真實(shí)的我而已。”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斯蒂芬作為藝術(shù)家的最后歸屬是由一位無(wú)知的教導(dǎo)主任肯定的。
教導(dǎo)主任問(wèn):“你是一位藝術(shù)家,是嗎,德達(dá)羅斯先生?藝術(shù)家的目標(biāo)就是創(chuàng)造美。”
斯蒂芬說(shuō):“只要視覺(jué)能理解它——我是說(shuō)美學(xué)理解——那它就是美的。”
斯蒂芬對(duì)同樣無(wú)知的同學(xué)林奇闡述美與藝術(shù)時(shí),藝術(shù)家的自我達(dá)到最高峰,一個(gè)完整的新柏拉圖主義、阿奎那思想的信徒便塑造完成了。斯蒂芬認(rèn)為:
“藝術(shù)是人為了審美目的對(duì)可覺(jué)察的或可理解的事物的處置。根據(jù)阿奎那,對(duì)令人愉悅的東西的穎悟就是美。美需要三樣特性:完整性、和諧和光彩。”
關(guān)于藝術(shù)形式,他認(rèn)為:
“你會(huì)發(fā)現(xiàn)藝術(shù)分為三種形式:抒情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藝術(shù)家以與自己最直接的關(guān)系來(lái)創(chuàng)造形象;史詩(shī)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藝術(shù)家以與自己和其他人間接的關(guān)系來(lái)創(chuàng)造形象;戲劇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藝術(shù)家以與其他人最直接的關(guān)系來(lái)創(chuàng)造形象。”
喬伊斯有意安排藝術(shù)家在闡釋自己關(guān)于美與藝術(shù)的觀點(diǎn)時(shí),他的聽(tīng)者是無(wú)知之徒,這使藝術(shù)家英雄的孤獨(dú)感達(dá)到了極致。于是,在我們面前呈現(xiàn)出一個(gè)完整的作為異端分子、作為英雄、作為流放者的英雄的藝術(shù)形象。
三
對(duì)喬伊斯來(lái)說(shuō),女人具有一種神秘的福樓拜式的神的力量。女人與創(chuàng)造和藝術(shù)密不可分。對(duì)斯蒂芬來(lái)說(shuō),藝術(shù)家無(wú)異于創(chuàng)世主。但神這個(gè)詞只有在圣母馬利亞想像力的子宮里才被肉化,也即是具象化。埃瑪成了斯蒂芬的圣母馬利亞,既是他的母親又是他的女友。被意象化的或被神化的女人——無(wú)論是玫瑰、鳥、處女想像力的子宮還是圣母馬利亞——都蘊(yùn)涵著斯蒂芬的愿望和作為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造力。喬伊斯甚至將“靈魂”也女性化。拉丁詞mulier(女人)對(duì)于斯蒂芬來(lái)說(shuō),具有柔和的美和令人沉醉的魅力。
在小說(shuō)出色地描述了視覺(jué)、聽(tīng)覺(jué)、嗅覺(jué)、味覺(jué)和觸覺(jué)的亞里士多德式的開(kāi)頭部分,在朦朧的孩提對(duì)一個(gè)完整的微觀世界的印象中,斯蒂芬對(duì)住在7號(hào)的萬(wàn)斯家的艾琳有好感。“他長(zhǎng)大后要娶艾琳做妻子”。但結(jié)果是災(zāi)難性的。他媽要他道歉,老鷹要飛來(lái)啄走他的眼睛。斯蒂芬無(wú)法接近她,因?yàn)樗切陆掏剑陆掏娇偸怯樞κツ格R利亞啟應(yīng)禱文。但他還是要鐘情于那一雙又長(zhǎng)又白的手,那手長(zhǎng)長(zhǎng)的,白皙而細(xì)瘦,那冰涼而潔白的東西就是象牙塔的含意。
有一天,他站在她身邊,手放在口袋里。她將手伸進(jìn)了他的口袋,他感覺(jué)到她的手多么冰涼、多么纖細(xì)、多么柔軟。她陡然縮回手,咯咯大笑著沿著小道的坡路撒腿跑開(kāi)去。她的金發(fā)在腦后隨風(fēng)飄拂起來(lái),猶如陽(yáng)光下的金子。這是斯蒂芬第一次對(duì)男女接觸的溫柔的感覺(jué)。斯蒂芬在這種接觸中總有一種未完成的惆悵。
在經(jīng)受了自我與權(quán)威的沖突之后,在斯蒂芬的夢(mèng)幻中出現(xiàn)了陰郁的復(fù)仇者的形象。這形象代表他童年時(shí)聽(tīng)說(shuō)與感覺(jué)到的怪異與可怕的一切。復(fù)仇的基督山伯爵的出現(xiàn)表明斯蒂芬心靈中孕育了反叛耶穌會(huì)教士、反叛教會(huì)教育的種子。而這種反叛的種子是與“美茜蒂絲光輝燦爛的形象”聯(lián)系在一起,與盛開(kāi)玫瑰的院子聯(lián)系在一起。但復(fù)仇者與女人的最終的結(jié)局是悲劇性的。美茜蒂絲嫁給了別人。在他們最后一次的會(huì)面中,復(fù)仇者終于作了一個(gè)憂郁的、傲慢的婉拒的手勢(shì)說(shuō):“夫人,我從不吃麝香葡萄。”他拒絕了女人的和解而成為英雄。對(duì)于藝術(shù)家來(lái)說(shuō),這是又一次完成的性。
在清澈的冬夜,斯蒂芬和埃瑪在末班馬車的踏板上聊天。斯蒂芬立在高一級(jí)的踏板上,埃瑪站在低一級(jí)的踏板上。談話間,她多次蹬到高一級(jí)的踏板上來(lái),然后又蹦下去,有那么一兩次她待在他的身旁忘了站下去了。后來(lái)還是踩下去了。要是她一直待在他身旁該有多好!該有多好!但是,埃瑪最終還是成了他賦寫的維拉涅拉詩(shī)中的妖婦。“她成了她的國(guó)家女性的一個(gè)形象,具有一顆蝙蝠般的靈魂,只有在黑暗、神秘與孤獨(dú)之中才有活力。”斯蒂芬和她成了陌路人,在圖書館臺(tái)階上他也沒(méi)有向她招呼。她一面玩弄著愛(ài)爾蘭語(yǔ)短語(yǔ)詞典,一面和莫蘭神父調(diào)情。斯蒂芬面對(duì)的是另一場(chǎng)失敗的令人惆悵的思念。“讓她去和神父調(diào)情,讓她去和那教會(huì)逗樂(lè)吧,那教會(huì)不過(guò)是基督教廚娘而已。”
斯蒂芬對(duì)女人的崇拜表現(xiàn)在他對(duì)圣母馬利亞的崇拜上。在他的心目中,圣母馬利亞并不是神,而是一個(gè)實(shí)實(shí)在在的女人。“一旦他真的想棄惡從善,一旦他真的想懺悔,那么,那令他感動(dòng)不已的沖動(dòng)便是希望成為她的騎士。”
喬伊斯式的藝術(shù)家英雄所崇尚的女人從艾琳、埃瑪、圣母馬利亞、美茜蒂絲而演變成“一只奇異而美麗的海鳥”,她代表了阿奎那式的美的極致。
有一位少女佇立在他面前的激流之中,孤獨(dú)而凝靜不動(dòng),遠(yuǎn)望著大海。她看上去像魔術(shù)幻變成的一只奇異而美麗的海鳥。她那頎長(zhǎng)、纖細(xì)而赤裸的雙肢猶如仙鶴的雙腳一樣纖美,除了肉身上留有一絲海草碧綠的痕跡之外,純白如玉。她那大腿,圓潤(rùn)可愛(ài),像象牙一樣潔白,幾乎裸露到臀部,游泳褲雪白的邊飾猶如輕柔雪白的羽絨。
貫穿在斯蒂芬的女人們的形象之中有一樣?xùn)|西是恒久不變的,那就是象牙,象牙塔。像象牙一樣潔白。象牙塔的形象出自《舊約·雅歌》第7章第1節(jié):“你的兩腿,圓潤(rùn)似玉,是藝術(shù)家手中的杰作。”在啟應(yīng)禱文中,圣母馬利亞被稱作“神秘的玫瑰”、“象牙塔”、“黃金屋”、“晨星”。所以,可以說(shuō),無(wú)論是艾琳、埃瑪、美茜蒂絲以及那海鳥般的少女都是圣母馬利亞的肉身化,世俗化。
極致的美的女人的出現(xiàn)意味著新的人生的來(lái)臨,意味著創(chuàng)造。喬伊斯1909年寫給諾拉·巴納克爾的信中,明確地表示他要將他與她的關(guān)系重建成一種母與子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因?yàn)閱桃了鼓赣H的死亡而斷絕了。對(duì)于喬伊斯來(lái)說(shuō),情人之間的關(guān)系太疏遠(yuǎn)了。他希冀一種更為緊密的關(guān)系:“哦,我希望我能像一個(gè)誕生于你的肉與血的孩子一般生存于你的子宮中,領(lǐng)受你的血液的哺育,在你的身體中那溫暖的神秘的黑暗中睡眠!”(《喬伊斯書信集》第1卷第296—297頁(yè))。跟喬伊斯一樣,斯蒂芬的靈魂跳將出來(lái)去迎接那創(chuàng)造的召喚:
去生活,去犯錯(cuò)誤,去沉淪,去成功,去從生命中創(chuàng)造生命!
正如哈佛大學(xué)教授哈利·列文指出的,這種野性的飛翔實(shí)質(zhì)上是一種性完成與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比喻。女人、女人想像力的子宮使斯蒂芬英雄最終完成了他的性的夢(mèng)幻,也即完成了他的藝術(shù)的受孕(構(gòu)想)、妊娠(醞釀)和生產(chǎn)(再現(xiàn))。在斯蒂芬看來(lái),“藝術(shù)家,正如造物的上帝一樣,存在于他創(chuàng)造的作品之中、之后、之外或之上。”斯蒂芬式的性與藝術(shù),性與創(chuàng)造的關(guān)系就這樣建立起來(lái)了。藝術(shù)的宗師每次將日常的經(jīng)驗(yàn)演繹成永恒的藝術(shù)時(shí),圣性的肉身化便再現(xiàn)一次。斯蒂芬成了他自己的母親。
四
在唯美主義者斯蒂芬看來(lái),自我總是處于與社會(huì)的不斷的沖突中,這便形成了藝術(shù)與人生的對(duì)立,藝術(shù)與宗教的對(duì)立。藝術(shù)和嚴(yán)峻的天主教是格格不入的,于是,藝術(shù)家從他開(kāi)始懂事起就與天主教傳統(tǒng)處于對(duì)立之中。他父親和耶穌的關(guān)系給少年的斯蒂芬以莫大的啟示。德達(dá)羅斯先生對(duì)“把上帝的神殿當(dāng)作投票站”作了抨擊。在虔誠(chéng)的丹特看來(lái),德達(dá)羅斯先生的家對(duì)教會(huì)大祭司毫無(wú)敬意。“德達(dá)羅斯先生往餐盤上‘叭’的一聲摔下他手中的刀叉。他說(shuō):‘敬意!愛(ài)爾蘭沒(méi)有上帝!在愛(ài)爾蘭,我們受夠了上帝的罪。打倒上帝!’于是,在斯蒂芬的心目中,宗教與肉欲的沖突,宗教與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沖突構(gòu)成了他青春成長(zhǎng)期心靈沖突的主要內(nèi)容。”
作為唯美主義者,他總感到自己會(huì)墮落。雖然他還沒(méi)有墮落,但他會(huì)默默地剎那間墮落的。要不墮落太困難了。他感受到他的靈魂正默默地往下滑去,掉墜下去,墮落下去,雖然還沒(méi)有掉入泥坑,還沒(méi)有完全墮落,但總要墮落的。野性在斯蒂芬的心靈中召喚著他。
在身體的覺(jué)醒中,斯蒂芬不再去謹(jǐn)慎斟酌他是否會(huì)侵犯天主教的戒律、犯重大的罪愆。他心中充滿了野性的欲望,而這種欲望在愛(ài)爾蘭天主教的環(huán)境中已壓抑了許久了。
他終于明白他自己的目標(biāo)是多么的愚不可及。他想筑起一堵秩序與典雅的防波堤以阻擋他外部生活的污穢的潮流,并用端行準(zhǔn)則來(lái)阻遏內(nèi)心強(qiáng)大潮流的沖擊。這一切全屬徒然。無(wú)論是從外部還是從內(nèi)部,水已經(jīng)漫溢過(guò)了他的堤壩:潮水再一次洶涌澎湃地拍擊業(yè)已傾頹的防波堤。
他熱切地順應(yīng)心中強(qiáng)烈的欲望,在這種欲望面前,其他的一切都顯得無(wú)關(guān)緊要而格格不入。他并不在乎他是否犯了不可饒恕的彌天大罪,他也不在乎他的人生成為一連串的欺騙與虛偽。除了他心中孕育的去犯滔天罪孽的粗野的欲念之外,沒(méi)有任何東西是神圣的。
在16歲的一天,他終于來(lái)到了都柏林的紅燈區(qū)。“他的熱血沸騰起來(lái)。他在那幽暗的、泥濘的街上孑然獨(dú)行,窺視著陰郁的小巷和門廊,熱切地聆聽(tīng)一切聲響。他像一只迷失的四處徘徊的野獸獨(dú)自呻吟起來(lái)。”
他感到有一個(gè)黑魆魆的精靈從黑暗中不可抗拒地爬上了他的身子。那路濟(jì)弗爾般的精靈難以捉摸,發(fā)出簌簌瑟瑟的聲響,猶如一股春潮,充溢了他整個(gè)的身子。“他在喉嚨間哽了如此長(zhǎng)時(shí)間的吶喊終于從他的嘴里噴吐而出。他的吶喊猶如煉獄受苦的人們發(fā)出的絕望的呻吟,吶喊在一陣強(qiáng)烈的懇求聲中漸漸銷聲匿跡,這是要求邪惡的不顧一切的縱情的吶喊,這吶喊僅僅是他在小便池濕淋淋的墻上讀到的淫褻的涂鴉的回聲而已。”
斯蒂芬閑逛走進(jìn)了狹窄而骯臟的小街。從那散發(fā)惡臭的小巷里,他聽(tīng)見(jiàn)了一陣陣嘶啞的騷動(dòng)和吵鬧聲,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們甕聲甕氣地唱著小調(diào)兒。娘兒們和小妞兒們身穿色彩鮮艷的長(zhǎng)袍,從一間屋子走到另一間屋子。她們的神態(tài)閑逸,散發(fā)出陣陣香水的味兒。一陣顫抖攫住了他,他的視線變得朦朧而模糊了。那橘黃色的煤氣燈火光在他刺痛的眼睛看來(lái)似乎往彌漫著霧靄的天空冉冉升起,猶如在神龕前燃燒一樣。在門前和點(diǎn)著燈火的廳堂里一群群人兒聚集在那里,排列有序,似乎在進(jìn)行什么儀式似的。他走進(jìn)了另一個(gè)世界:他從數(shù)百年的沉睡中蘇醒過(guò)來(lái)了,從中世紀(jì)式的禁欲中解脫出來(lái)了。
一個(gè)身穿粉紅長(zhǎng)袍的年紀(jì)輕輕的女人將手搭放在他的手臂上一把拉住他,雙眼直視他的臉龐。她快快活活地說(shuō):“晚安,親愛(ài)的!”他便進(jìn)了她的房間。他閉上了雙眼,將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全部付與了她。在這世界上,除了她那微啟的嘴唇的輕壓以外,他什么也感覺(jué)不到了。她的嘴唇壓在他的腦海上,就像它們壓在他的嘴唇上一樣,仿佛它們是一種模糊的語(yǔ)言工具似的。
斯蒂芬的罪愆是宗教所不能容許的。在充滿宗教氣氛的公學(xué)中,他的精神處于極端的痛苦與惶恐之中。恐懼(fear)左右了他的生活。恐懼甚至使人進(jìn)入一種“舔舔嘴唇上油漬”的野獸狀態(tài)。阿納爾神父在課堂上宣講地獄的苦難,讓斯蒂芬不寒而栗。上帝創(chuàng)造了地獄之火來(lái)折磨、懲罰不知改悔的罪人。無(wú)止境地永恒地燃燒的火的煎熬是讓遭天譴的人蒙受的最痛苦的磨難。他在是否去教堂懺悔的問(wèn)題上極端矛盾。他開(kāi)始自責(zé)。宗教的力量戰(zhàn)勝了他靈魂中野性的欲念。他感到一種恐懼,這種對(duì)死后命運(yùn)的恐懼左右了他的靈魂。他的靈魂這時(shí)浸透了宗教的思想。“他星期日思考神圣三位一體的奧理,星期一思忖圣靈,星期二考慮守護(hù)神,星期三思索圣約瑟,星期四沉思享受上帝至高祝福的祭臺(tái)圣餐禮,星期五深思受苦受難的耶穌,星期六冥想為主所寵愛(ài)的圣潔的圣母馬利亞。”這表明了斯蒂芬在思想上和行動(dòng)上的皈依。他在創(chuàng)造世間萬(wàn)物和人的上帝面前感到敬畏,感到自卑。“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靈魂通過(guò)自己的肉體無(wú)論在思想上,在言語(yǔ)上還是在行動(dòng)上都肆意犯罪了。懺悔!他不得不坦白每一個(gè)罪孽。”
雖然斯蒂芬因懼怕地獄而去一座偏僻的小教堂懺悔,但宗教仍然不可能羈絆住他。在斯蒂芬心靈歷程的演變中,即使當(dāng)他全身心醉心于宗教時(shí),在圣餐禮上,他被《雅歌》中的形象所召喚,關(guān)注的是inter ubera mea commorabitur(讓他在我的兩乳間安臥)、“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lái),與我同去。”(《舊約·雅歌》2:13)斯蒂芬懇請(qǐng)靈魂起來(lái),就像去赴結(jié)婚典禮一樣,并遠(yuǎn)走高飛,懇請(qǐng)她往下觀望,一個(gè)從亞瑪拿山巔、從豹子山崗來(lái)的佳偶正在那里。他的唯美的靈魂重又充斥了揮之不去的人性的肉欲的聲音,肉欲的呼聲在他祈禱和默想時(shí)又在他耳邊絮聒不止了。天主教在與世俗的享樂(lè)的抗?fàn)幹性谒沟俜业撵`魂里終于失敗。甚至在懺悔與祈禱之中,在罪愆與懺悔的交替之中,肉欲仍然一直在誘惑他年輕的心。這種誘惑是如此強(qiáng)烈,使他決意背棄自己做過(guò)的懺悔。他知道世界上充滿了罪愆的陷阱,他甘愿讓靈魂像伊卡洛斯一樣靜靜地沉淪下去。這樣他可以在心靈的自由與力量之中驕傲地創(chuàng)造出新的、有生命力的、美麗的、永遠(yuǎn)不會(huì)滅亡的東西來(lái)。他的墮落的罪孽成為發(fā)現(xiàn)自我和人生的重要的一部分。
在第三章,喬伊斯讓阿納爾神父長(zhǎng)篇累牘地演講天主的恩澤、耶穌的慈愛(ài)與地獄的可怖,其重要的用意就是要反襯出宗教的虛偽。一切恐怖與恫嚇的詞都用絕了,詞也就不成其詞,也就更暴露出其空洞無(wú)物,其虛妄和偽善。
耐人尋味的是,喬伊斯在第五章開(kāi)頭用“淡茶”、“炸面包皮”暗喻了斯蒂芬在心靈中經(jīng)歷了圣化彌撒的一幕,斯蒂芬作為藝術(shù)宗師親吻代表耶穌的圣壇。喬伊斯使斯蒂芬變成了耶穌,這就意味著斯蒂芬親吻自己。瘋嬤嬤的呼喊“耶穌,啊!耶穌,耶穌!”暗喻在感恩彌撒上,斯蒂芬被命名為耶穌。喬伊斯在斯蒂芬抵達(dá)國(guó)家圖書館時(shí),又暗喻斯蒂芬被象征性地釘上了十字架。斯蒂芬在國(guó)家圖書館的臺(tái)階上面對(duì)埃瑪——圣母馬利亞的肉身化,于是在雨中圣性的肉身化和斯蒂芬被釘上十字架的象征便結(jié)合在一起了。斯蒂芬英雄實(shí)質(zhì)上是一個(gè)受難的“耶穌”,一個(gè)反叛天主教的“耶穌”。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斯蒂芬與宗教的斷裂是通過(guò)他違背母命來(lái)表現(xiàn)的。在他孩提最初的嗅覺(jué)中,“他媽散發(fā)出一種比他爸好聞得多的味兒”。但他一直與媽媽處于沖突之中。當(dāng)她希望他在復(fù)活節(jié)接受圣職時(shí),他與媽媽公開(kāi)決裂了。
當(dāng)斯蒂芬獨(dú)自行走在基德?tīng)柦稚蠒r(shí),有人一把死死抓住他的胳膊,那是克蘭利。
斯蒂芬說(shuō):“今晚我吵嘴了,很不痛快。”
“跟家里的人?”
“跟我母親。她希望我復(fù)活節(jié)接受圣職。”
“你愿意嗎?”
“我不愿意。我不想伺候上帝。”
“你知道嗎,真是奇怪,你的心靈浸透了宗教,而你還說(shuō)不信教。你在學(xué)校里的時(shí)候信教嗎?”
“我那時(shí)信教。”
“你那時(shí)快樂(lè)一些嗎?”
“常常快樂(lè),又常常不快樂(lè)。我那時(shí)不是現(xiàn)在的我,不是我必須成為的那種人。我試圖去愛(ài)上帝,我失敗了。非常難。”
克蘭利問(wèn):“你腦子里想過(guò)嗎,耶穌并不是如他裝模作樣做出來(lái)的樣子?”
“產(chǎn)生這個(gè)疑問(wèn)的第一個(gè)人是耶穌自己。”
“你也不想成為新教徒?”
“我說(shuō)過(guò)我已喪失了信仰,但我還沒(méi)有喪失自尊。放棄了一種合乎邏輯、嚴(yán)謹(jǐn)而荒唐的信仰,而去擁抱另一個(gè)不合邏輯、雜亂不堪的荒唐的信仰,算什么解放呢?”斯蒂芬接著說(shuō),“我可能得遠(yuǎn)走高飛了。”
“到哪兒去?”
“到我能去的地方。”
“我記得你曾說(shuō)過(guò),去尋覓、發(fā)現(xiàn)一種生活方式或藝術(shù)方式,你的精神可以在其中毫無(wú)阻攔地自由表達(dá)。”
“喂,克蘭利,我不想伺候我不再信仰的東西,不管那稱之為我的家,我的祖國(guó)或者我的教會(huì):我將在一種生活或藝術(shù)方式中盡量自由自在地、盡量完整地表達(dá)我自己,我將使用我允許自己使用的惟一武器來(lái)自衛(wèi)——那就是沉默、流放和狡黠。”
這一段對(duì)話對(duì)于理解斯蒂芬思想的脈絡(luò)在全書中是至關(guān)重要的。它表明:(1)斯蒂芬是在一個(gè)具有濃厚的天主教氣氛的都柏林社會(huì)與家庭中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他的心靈里浸透了宗教;這是斯蒂芬情感悲劇的根源;(2)他曾試圖去愛(ài)上帝,但因?yàn)槿庥c美學(xué)的原因,和路濟(jì)弗爾一樣,他不想伺候上帝;(3)他懷疑,要是圣餐禮上的酒變酸而成醋,獻(xiàn)祭的面包發(fā)霉變質(zhì),那么耶穌基督作為上帝和作為人是否還存在于其中:他失去了對(duì)耶穌的信仰,因?yàn)橐d只是一個(gè)裝模作樣的形象,連耶穌自己都不相信自己;(4)他認(rèn)為,一切宗教信仰都有可能使他喪失自我、喪失自尊。他想獲取自我的解放,必須摒棄一切信仰;(5)他的生活的目標(biāo)就是在一種生活或藝術(shù)方式中盡量自由自在地、盡量完整地表達(dá)自我。
斯蒂芬——這個(gè)“具有永恒想像力的祭司”——是在給同學(xué)林奇在運(yùn)河大橋闡述阿奎那的美學(xué)觀(對(duì)令人愉悅的東西的穎悟就是美)之后不久,決意作出違抗母命的決定來(lái)的。阿奎那的美學(xué)觀和“一種恣肆放任的充滿少年美的”偶像破壞的易卜生精神是斯蒂芬決定與宗教決裂的思想基礎(chǔ);而斯蒂芬的最終的解放仍具體體現(xiàn)在一個(gè)新的藝術(shù)方式中得到自由表達(dá)的權(quán)利,是自我流放。這可以說(shuō)是一個(gè)唯美主義者對(duì)天主教的宣言。正是斯蒂芬對(duì)宗教的反叛,正是他對(duì)于拒絕感官快樂(lè)的生活的懼怕,使他義無(wú)反顧地走上了藝術(shù)的道路,走上了探索美的真諦的道路,走進(jìn)了自我流放的精神家園。
因?yàn)檫@樣,斯蒂芬向世界宣告,他不會(huì)為任何他不再皈依的信念去獻(xiàn)身,不管那是他的家、他的祖國(guó)或者是他的宗教。他要自由自在地完整地在人生和藝術(shù)的方式中去表達(dá)自己,而他的武器便是:緘默、流放、狡黠。最終,他將自己從小資產(chǎn)階級(jí)家庭、愛(ài)爾蘭與天主教中脫離出來(lái),希望靈魂自由自在,想像也自由自在,像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一樣試圖擺脫民族、語(yǔ)言與宗教的羈絆,他成為一個(gè)永恒的孤獨(dú)的英雄。
在小說(shuō)的結(jié)尾,喬伊斯將小說(shuō)的第三人稱戲劇性地改為第一人稱,用日記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據(jù)艾琳·亨迪·蔡斯,這是一種升華,從生物學(xué)意義上的升華(童年—成年)到心理的與道德的升華,也即從被動(dòng)的接受到自我意志。在日記中,行將自我流放的青年藝術(shù)家斯蒂芬寫下:離去吧!離去吧!歡迎,哦,生活!我將百萬(wàn)次地去迎接現(xiàn)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在我的靈魂的作坊里去鍛冶我這一類人尚未被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良知。
在這里,喬伊斯表述了他的美學(xué)理論的基礎(chǔ)。他認(rèn)為自我主義是不可磨滅的,自我主義是“救世主”;藝術(shù)家是“一個(gè)擁有永恒想像力的教士,一個(gè)能將日常的經(jīng)驗(yàn)演化成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光輝燦爛的東西的人”。斯蒂芬也跟喬伊斯一樣,只相信“自己的靈魂”,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斯蒂芬終于在與天主教的決裂中找到了自我,“靈魂自由,想像自由馳騁”,他找到了真正的“救世主”——他自己的靈魂,“誕生以體驗(yàn)”,實(shí)踐了喬伊斯的美學(xué)理論。
五
喬伊斯對(duì)他的斯蒂芬·德達(dá)羅斯的態(tài)度是什么呢?這是國(guó)際學(xué)術(shù)界多年來(lái)一直爭(zhēng)論不休的問(wèn)題。
約翰·V·凱萊赫認(rèn)為,喬伊斯對(duì)斯蒂芬懷有一種復(fù)雜的感情。他一方面認(rèn)為斯蒂芬相當(dāng)學(xué)究氣,另一方面懷著譏諷的態(tài)度來(lái)描述他。也就是說(shuō),喬伊斯一方面同情他,另一方面對(duì)他懷有一種柔和的、幽默的自豪感。休·肯納認(rèn)為,斯蒂芬僅僅是一個(gè)裝模作樣的唯美主義者,而不是一個(gè)真正的或者可能成為的藝術(shù)家。
持有與凱萊赫和肯納相同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認(rèn)為,喬伊斯把斯蒂芬看成是一個(gè)自傳性的主人公,他戰(zhàn)勝了污穢、愚蠢、叛變的環(huán)境,與家庭、民族、教會(huì)決裂去尋覓自己(或者說(shuō)“靈魂”)的歸屬。
有的學(xué)者如威廉·約克·廷達(dá)爾則認(rèn)為,喬伊斯將斯蒂芬看成是作家的自傳性的代表,一幅由一位年長(zhǎng)的長(zhǎng)者描摹的“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他認(rèn)為,小說(shuō)標(biāo)題中的“作為青年的”短語(yǔ)是至關(guān)重要的,斯蒂芬不是喬伊斯,而是過(guò)去的喬伊斯。在創(chuàng)作《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時(shí),喬伊斯作為一個(gè)成熟的人回眸他的青春期的自我;他這樣做,并不是要歌頌他,而只是給予藝術(shù)家應(yīng)得的那一份罷了。斯蒂芬只是喬伊斯手中的材料而已。正如所有的藝術(shù)家那樣,他沉迷于他的材料之中,通過(guò)寫作,他給這些材料以正式的形式,并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他創(chuàng)造了這個(gè)富有個(gè)性的人物,并賦予它以象征的形式,這樣,象征的形式一旦擺脫了情感與個(gè)性,便會(huì)提供進(jìn)一步審視現(xiàn)實(shí)的可能性。
肯尼思·伯克則認(rèn)為,喬伊斯對(duì)寄托在斯蒂芬身上的自己的過(guò)去的感情是復(fù)雜的,它既含有揶揄,又含有浪漫與同情感。但斯蒂芬絕不是喬伊斯。這可以在喬伊斯對(duì)朋友弗蘭克·勃金說(shuō)的話中得到證實(shí)。喬伊斯曾經(jīng)對(duì)他評(píng)論斯蒂芬時(shí)說(shuō):“我沒(méi)能讓這位年輕人過(guò)輕松的日子,是嗎?”他還說(shuō):“我對(duì)這位年輕人太苛刻了。”
里查德·埃爾曼與廷達(dá)爾的看法在本質(zhì)上相近。他認(rèn)為,喬伊斯回憶敘述他的過(guò)去,主要是為自己的過(guò)去辯護(hù),而不是為了揭露它。他認(rèn)為,喬伊斯的“藝術(shù)的受孕、妊娠和生產(chǎn)”比喻是理解《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的關(guān)鍵。藝術(shù)家在描摹他的畫像的過(guò)程中,便成為“他自己的母親”;他“似乎重組了他的家庭關(guān)系,將他自己從作為一個(gè)孩子對(duì)自己看法的矛盾中擺脫出來(lái),以充分地利用這些矛盾,克服他母親的庸俗和對(duì)父親的憎恨,成為他自己的母親和父親,通過(guò)超人的創(chuàng)造性的過(guò)程,變成詹姆斯·喬伊斯,而不是任何別的人”。
喬伊斯確實(shí)是在自己最初20年的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的。作家創(chuàng)作的這類小說(shuō)被稱為藝術(shù)小說(shuō),或者說(shuō)描述藝術(shù)家成長(zhǎng)的小說(shuō)。這類小說(shuō)帶有強(qiáng)烈的自傳的性質(zhì)。但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終究是一個(gè)帶有強(qiáng)烈的想像力色彩的創(chuàng)造過(guò)程。它不可能是生活的原封不動(dòng)的翻版,也不可能是生活的簡(jiǎn)單的再現(xiàn)。縱然小說(shuō)主人公帶有作家的氣質(zhì),帶有他的優(yōu)點(diǎn)和缺憾,他的期望和野心,但小說(shuō)主人公不可能是作家本人。喬伊斯在與朋友勃金的談話中帶有的那種揶揄的語(yǔ)調(diào)表明,他是站在高處,在一個(gè)遠(yuǎn)處審視他的主人公的。作家的經(jīng)驗(yàn)、生活和靈魂通過(guò)想像力的作坊的鍛冶便成為新的濃縮的賦予了暗喻、比喻和象征意義的經(jīng)驗(yàn)、生活和靈魂。正如喬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拉斯寫的,“《青年藝術(shù)家畫像》不是一部自傳,而是一部藝術(shù)創(chuàng)作。”(見(jiàn)哈利·列文:《詹姆斯·喬伊斯》1960年新方向版)所以,斯蒂芬是喬伊斯,又不是喬伊斯,這就是結(jié)論。
朱世達(d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