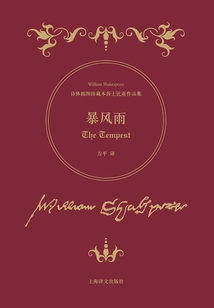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欣賞這個飛翔在現實生活上空的傳奇性喜劇《暴風雨》需要浪漫主義的情懷。
莎士比亞創作他最后一個詩劇《暴風雨》的時候,已飽經了一番人間滄桑。伊麗莎白時代的繁榮景象如同薄霧似的在逐漸消散,潛伏著危機的社會陰暗面闖進了詩人的創作視野;在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年代里,他感受到山雨欲來的沉重氣氛。洋溢在他早期喜劇中那種樂觀主義的精神消失了,但是不能因此認為,人文主義者所抱的理想也化作塵土,隨風而去了。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美好的,這該是莎士比亞這位人文主義者始終堅持的信仰。我們且聽聽蜜蘭達的這一段情緒激蕩、像一曲贊歌似的表白吧:
噢,奇妙啊!
瞧這兒,那么多風度不凡的人兒!
人類是多美好啊!這個新世界多棒呀,
有這么好的人們![1]
中世紀天主教會以神性壓抑人性,宣揚天國,否定人世。現在,蜜蘭達的那一曲贊歌不再是對神的禮拜,而是在熱情地歌頌人:“人類是多美好啊!”
把信仰捧回人間,交托給人類自己,這很了不起。在人文主義者的這一優秀的詩劇里,我們可以辨認出歷史的進程的蹤跡。[2]
“人類是多美好啊!”這就是《暴風雨》的一個富于詩意的主題思想,是劇作家一心一意要向觀眾傾吐的肺腑之言。你也可以說,這就是杰出的人文主義者企圖通過他最后一部作品,向遙遠的后人傳遞的一個信息;這是詩人行將離開人間,在為人類的未來祝福。
如果從這一角度去理解《暴風雨》,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了整個戲劇構思。
為什么要在那洶涌的萬頃波濤里浮現出那么一個虛無縹緲的海上仙島?不錯,你很可以說,這里有逃避現實的因素在內;但是劇作家還另有一番用心呢:可以讓蜜蘭達,這個從來沒有機會和人類交往的姑娘(現在正沉浸在幸福的愛情里),抬起眼來,忽然發現一個嶄新的世界和那么多風度不凡的人兒展現在面前!這時候還有誰可以和她的驚訝、她的喜悅、她的興奮相比呢?莎士比亞正是抓住了這最富于戲劇性的一剎那,好讓她不能抑制的激情不但給人一種藝術上的真實感,而同時又用最清新的詩意表達出來。
“這個新世界多棒呀!”這一聲天真無邪、充滿著信任感的驚嘆,直到今天聽來,并沒有失去那一股直撲心靈的力量。它那清新的詩意取得了一種高出于現實的象征意義,使我們不過多地停留在蜜蘭達眼前的近景;這里只是展列了一些來自污濁的舊社會的人物(要是當真把他們看成了人類最優秀的代表,那真是一種諷刺了)。可是那詩意的激情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喚起了我們的理想,引導我們矚目于一片美好的遠景——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將為它的誕生而終身奮斗的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
當蜜蘭達站在海岸邊,遙遙地望見海船在驚濤駭浪中翻滾,船上的人們正在狂風暴雨中絕望地掙扎時,她忍不住痛苦地絞著雙手,嚷道:
唉,看那些人受難,我跟著在受難![3]
詩人用浪漫主義的手法塑造出了這一隔絕在人類社會之外,“聞足音跫跫然則喜”的蜜蘭達的形象;她多么渴望身處于正在遭難的人們中間,和他們共呼吸、同命運啊。在蜜蘭達的無限深情里,我們仿佛聽到了劇作家本人的心聲。而一葉危舟在怒海中掙扎,在詩人的形象思維里,也許已和無數的人們在苦難的現實生活中顛仆翻滾的情景融合在一起了。
蜜蘭達一上場和最后下場前的那兩段充滿激情、富于詩意的表白,我個人認為是詩劇《暴風雨》中最難使人忘懷的部分。也許我們很可以選取這首尾呼應的兩段話當做銘文,鏤刻在莎士比亞的紀念碑上吧。一個人文主義者熱愛人世、歌頌人世的精神,充分體現在這里了。
十六世紀的英國,在封建王國的內部,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速發展,階級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但是盤踞在社會階梯頂端的還是英國皇室和大封建貴族,門閥世家還是受到習慣勢力的崇拜和羨慕。這特別在婚姻問題上表現出來。在《李爾王》里,為人文主義思想鼓舞的法蘭西國王可以毫不猶豫地娶沒有分文陪嫁的公主為王后,但是很難想像:法蘭西國王會娶一個陪嫁豐厚、卻沒有身份的小家碧玉。
恩格斯曾經這樣論述過,“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之后,結婚的充分自由才能實現,那時候,男子“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得婦女的獻身;而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也永遠不會再出于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于男子……”[4]
把個人婚姻的充分自由和階級社會(以及階級偏見)的最終消滅,聯系到一起來認識,得出了這么深刻的見解,那是不可能為十七世紀初的人們所掌握的。但莎士比亞在寫出他晚年的最后幾個喜劇時,這樣一個問題似乎經常朦朧地出現在他的思考里:
能不能設想,真誠的愛情,除了本人值得被愛慕的品質外,再不需要其他任何外加的先決條件呢?
在《結局好萬事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里,莎士比亞接觸到這個問題,對于血統論提出了懷疑(第二幕第三景)。但是這一戲劇實際上寫的并不是真誠的愛情,只是誤用感情的少女的一片癡心罷了——一個平民姑娘愛上了并不值得她愛的貴族青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冬天的故事》。王子愛上了牧羊女,為了她,向天宣誓道:
把我王嗣的名分一筆勾銷了吧,父親!
我是我愛情的繼承人![5]
這在婚姻觀念上幾乎可以算得是一個突破了。最后發現,這位儀態萬方的牧羊女原來就是流落在民間的公主,她一恢復金枝玉葉的身份,當然什么阻礙也沒有了。有情人終于成了眷屬。
《暴風雨》中,蜜蘭達和王子的機遇,可以說是《冬天的故事》中的愛情主題的再現。兩個喜劇的寫作時期先后銜接,而愛情的主題又相互呼應,這說明了這里存在著莎士比亞一直在思考、探索、試圖接近的一個問題。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卻是一個很難得到圓滿解答的問題。
具有民主思想萌芽的莎士比亞處理這個主題時,似乎有些羞羞答答,他沒有用豐滿的藝術形象清晰地表達這樣一個見識:真誠的愛情應該和門第觀念——封建貴族的階級偏見——徹底決裂。還是保留著那“王子與公主”的外殼——仿佛這是一塊少不了的“遮羞布”。莎士比亞的思想領域里似乎有一塊始終沒有能突破的禁區吧。或許呢,考慮到戲劇不同于詩歌小說,必須照顧到觀眾的欣賞習慣和演出效果(更何況這個傳奇劇是為宮廷演出而寫作的),[6]可以這樣說吧:這里是莎士比亞作為戲劇家(因此必然會受較多的社會條件約束)所沒有能最后跨越的一個思想高度。這半步之差說明了人類在歷史的長河里所積累起來的點滴進步來之不易,值得后人的珍惜。
《暴風雨》里的愛情,仍然是王子與公主的愛情,但他們又是在烏托邦式的仙島上,失去了自己的社會身份的情況下,相遇而相愛的。門第觀念被暫時擱置在一邊了。一等到戀愛成熟,劇作家把落難公主的身份交還給蜜蘭達,她就成了不開口的啞角。于是傳統的那一套:門當戶對,榮華富貴、皆大歡喜的婚姻結束了這個喜劇。
海上仙島和這島上的傳奇故事原是向壁虛構,可是在蜜蘭達身上卻自有一些東西使人難以忘懷。她仿佛當真是在那清風明月的大自然懷抱中長大起來的少女,不僅沒有沾染矯揉虛浮的宮廷習氣,她那純潔質樸的心靈仿佛還是一塊完整的、沒有刀斧痕跡的美玉:她幾乎不曾感受到千百年來習慣勢力所加于婦女身上的束縛,她能夠毫無拘束、不加掩飾地把內心深處最隱蔽的思想感情,向她第一個遇見的、為她所喜歡的異性吐露出來,出言吐語又是那樣單純明凈,在復雜的、有過多計較的現實生活中,哪里去找這樣一位純情的少女,坦然地向對方捧出自己一顆赤誠的心:——
我從沒見識過
跟我是姐妹的女性,在我的心靈中
也從沒印進過一個女人的臉蛋——
除非在鏡子里我照見了我自己;我也
從沒見到過哪一個,我能稱他為
男人——除了你,好朋友,和我那親爸爸。……
除了你,我再不希望跟別人做伴;
也想像不出,除了你,我還能喜歡上
另一個形象。[7]
可愛的蜜蘭達似乎借給人一雙幻想的翅膀,好飛向遙遠而美好的未來。當一個新的時代來到,婚姻真正有了充分的自由,人們“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就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了”。在那嶄新的世界里,婦女在處理工作、家庭、生活的問題時,將顯示出怎樣不凡的風度和精神面貌呢?可愛的蜜蘭達似乎讓我們在一瞥之間窺見了她們的面影。當她們愛上了自己所喜愛的小伙子,而吐露自己的情懷時,自然會有不同于蜜蘭達的那一番求愛(其實是求婚)的表白,但是想必也同樣地那么單純、坦率、主動——
我是你的妻,要是你愿意娶我;
要不,我一輩子都做你的侍女。
跟你做伴侶,也許你會拒絕我;
可是我情愿做你的奴婢,不管你
要我不要我。[8]
傳說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我們不由得想起了莎士比亞筆下的普洛士帕羅。莎翁像上帝似的在創造《暴風雨》中這個呼風喚雨的主人公時,想必忘情地把自己也寫進去了吧。從魔法大師普洛士帕羅的使人難忘的出言吐語里,我們似乎聽到了藝術大師莎士比亞本人的口吻。創造者和被創造的,在我們的想像里似乎合二為一了。
為了給一對年輕的情人來點兒消遣,普洛士帕羅施展法術,映現出海市蜃樓的奇景異觀;當一幕幕幻象變為過眼煙云,悄然消散后,他不無得意地夸耀魔法的神秘莫測就在于無中生有:
我們這些個演員,
我說過,原是一群精靈,全都
化成了一縷煙,淡淡的一縷煙云。
正像這一場無影無蹤的夢幻:
那高入云霄的樓臺,輝煌的宮殿,
宏偉的廟宇,以至整個兒地球——
地面上的一切,都將煙消云散,
也會像那虛無縹緲的熱鬧場面,
不留下半點影痕。
這位老法師談他的魔法,不有些像藝術家在談他的藝術觀嗎?
創作離不開現實生活,藝術來自現實;然而她又必須學會怎樣張開想像的翅膀,超越現實,彌補現實的缺憾。這一點,莎翁作為營造一個“舞臺小天地”的戲劇家,最有深刻的體會了。他的歷史劇《亨利五世》就是這么向觀眾呼吁的:“用你們的想像彌補我們的貧乏吧!”
假使要問:藝術的生命在哪里?在不同的場合,莎翁可能會有不同的回答。例如在強調藝術和現實的關系時:“舉起鏡子照自然”(《哈姆萊特》)等。但是我相信,在創作這個發生在海外仙島的傳奇劇時,他的回答會是:藝術的生命在于呼喚起想像——正好比不許無中生有,不讓制造幻覺,就沒有魔法存在的余地。
因此揮舞著魔杖的普洛士帕羅在這里談的是魔法,卻簡直就像替藝術大師莎翁(他同樣手握著一支能創造藝術奇跡的魔筆)道出了他的藝術觀。
莎翁的一生是和舞臺生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一生。對于他,舞臺就是人生的縮影,劇場就是一個具體而微小的天地。植根在這一特殊的小天地的藝術觀,很容易和莎翁的閱盡滄桑的人生觀融合在一起,進入了對人生的哲理性的、也是戲劇性的思考——從“舞臺小天地”擴伸為“人生大舞臺”的嗟嘆。
這樣,主人公的華彩樂段似的上述談吐,輕輕一轉,就成為對人生的無限感慨,對生命的大徹大悟,而且因為這里充滿著雋永的詩意,也就格外地發人深思:
論我們這塊料,
也就是憑空織成那夢幻的材料。
我們這匆匆一生,前后左右,
都裹繞在睡夢中。
我們知道,《暴風雨》是莎翁的“天鵝之歌”。在創作了那么多喜劇的、悲劇的、歷史劇的杰作后,二十年輝煌的藝術生涯從此結束。在這最后一部杰作的最后一幕里,普洛士帕羅在仙島上施展了種種興風作浪、驚心動魄的魔法之后,自表決心道:
我就此折斷
我的魔杖,埋進在地底的深處,
我那魔法書,拋進海心,由著它
沉到不可測量的萬丈深底。
那脫下法衣、折斷魔杖、決心離開仙島,行將回歸故鄉終老的米蘭公爵讓人產生了幻覺,在他的形象后面,仿佛讓人看到了將要擱筆的莎士比亞——他那支彩筆也具有魔法似的曾經創造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男男女女。這是當時倫敦最受歡迎的劇作家在退出舞臺之前,向他親愛的觀眾做最后的告別啊。
他筆下的米蘭公爵,很知道一旦“再沒有精靈好驅使,再沒有魔法和符咒”,剩下的就只是一個“年衰體弱”無能為力的老頭兒(見“收場白”);同樣地,莎翁不是不明白,他一旦拋下使人著魔的詩筆,告別了那有聲有色的舞臺天地,他亦將歸絢爛于平淡,無所作為,只是失落在蕓蕓眾生中,一個年衰體弱的老人罷了。
文筆還是那么遒勁,詩意還是那么濃郁,文思還是那么活躍,對人性的觀察還是那么深刻入微,好戲還沒唱完呢——卻戛然而止,已成絕唱了。當時人生的旅程苦于太匆促了,早婚,早育,到了五十光景,從現代人說來,正當是成熟、收成的年代,在四世紀前,卻已是步入人生的晚景,該了卻塵世的宿緣了。
不同于以前的莎劇,《暴風雨》給了我們一種特殊的親切感,只覺得偉大的劇作家從沒有離得我們這么近,我們仿佛傾聽到了他的內心獨白——綠波上輕輕飄揚起一曲“天鵝之歌”。
注釋:
[1]見第五幕第一景。
[2]見第五幕第一景。
[3]見第一幕第二景。
[4]見《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78、79頁。
[5]見該劇第四幕第四景。
[6]根據可以查考的資料,《暴風雨》于1611年11月1日,及1612-1613年間,兩度在宮廷演出,第二次是為了慶賀王室的婚禮。為宮廷演出而編寫劇本,自然免不了使劇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受到很大的限制。
[7]見第三幕第一景。
[8]見第三幕第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