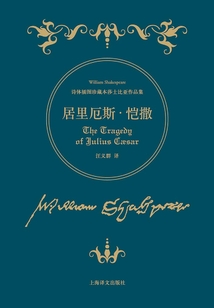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1599年上半年,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環(huán)球劇場”新落成,首演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以早期習作《亨利六世》開頭的一系列深受觀眾歡迎的英國歷史劇,到此畫上了圓滿的句號。那一年秋天,又上演了古羅馬歷史劇《居里厄斯·愷撒》。進入創(chuàng)作巔峰狀態(tài)的莎士比亞,從此把他的才華轉(zhuǎn)向了悲劇領(lǐng)域,一系列驚心動魄的大悲劇將相繼而來,首先問世的是世紀之初的《哈姆萊特》(1600)。
在莎士比亞的創(chuàng)作道路上,處在歷史劇《亨利五世》和悲劇《哈姆萊特》之間的《居里厄斯·愷撒》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
英國向來奉行的是君權(quán)神授的封建政治體制,從沒有像古羅馬那樣,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貴族共和國的政治經(jīng)驗。[1]《居里厄斯·愷撒》中以勃魯托斯為首的小集團所竭力維護的幾乎名存實亡的四百多年來的古羅馬共和政體,因此不會是劇作家本人的一種政治理想。
莎士比亞所向往的應(yīng)是在開明君主統(tǒng)治下的一個打破封建割據(jù)、中央集權(quán)的統(tǒng)一的王國。出現(xiàn)在他的歷史劇中奮發(fā)有為、一代英主的亨利五世以及收拾殘局、重整乾坤的亨利七世(見《理查三世》)的形象,多少帶有理想色彩,在他們的身上寄托著劇作家的政治理想——只有在精明強悍又寬厚仁愛的國王的統(tǒng)治下,才會出現(xiàn)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太平盛世。劇作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國王懦弱無能、被挾持、被推翻或被謀殺,梟雄紛起,國家陷于四分五裂,戰(zhàn)火連綿、民不聊生。在以三十年內(nèi)戰(zhàn)(玫瑰戰(zhàn)爭)為背景的《亨利六世》三聯(lián)劇中,清楚地表達了劇作家的(以及英國人民)這一政治焦慮。
現(xiàn)在,在古羅馬歷史劇中,雄才大略的愷撒遇刺身亡,而反對黨無論在威望或政治才干上都不足以取而代之。羅馬的政權(quán)因而出現(xiàn)了真空狀態(tài),兩個敵對黨派隨即兵戎相見。勃魯托斯一派倒下后,奪取了政權(quán)的安東尼、屋大維之間又展開了內(nèi)部的斗爭。將近二十年,國無寧日。這一切恰好印證了莎士比亞在英國歷史系列劇中一再表達的政治憂思。因此可以這樣說,往事越千年的羅馬史劇與早期的英國歷史系列劇自有著內(nèi)在的呼應(yīng)。
另一方面,這一羅馬歷史劇在莎劇原始版本(1623)中被歸入悲劇類,全稱是《居里厄斯·愷撒的悲劇》。實際上,它同時也是另一位主人公勃魯托斯的悲劇。劇作家讓我們清楚看到他個人的悲劇可以歸結(jié)為性格的悲劇。他的形象幾乎預(yù)告著在下一部悲劇中一個不朽的典型人物:哈姆萊特的誕生。相繼而來的一系列大悲劇中的主人公,他們所遭受的挫折、他們的幻滅感、對人生的疑問,以及最后的倒下,正是建立在他們各自的內(nèi)在的悲劇性格上。
因此很可以說,在政治思想以及在創(chuàng)作手法上,《愷撒》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在莎翁創(chuàng)作道路上處于一個令人矚目的轉(zhuǎn)折點。
試圖為羅馬歷史劇中的主要人物作出較客觀的評價,需要認清這樣一點:勃魯托斯所標榜的“共和政體”(commonwealth)和我們現(xiàn)代政治概念上的民主政治絕不是一回事。
愷撒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后,羅馬元老院里響徹了暗殺者們的歡呼聲:“自由啦!解放啦!暴君死啦!”“自由啦!解放啦!翻身啦!”(liberty!freedom,and enfranchisement!)最后由勃魯托斯率領(lǐng)著小集團,一起揮舞著用愷撒的鮮血染紅的利刃,走向羅馬市場,他帶頭高呼:“自由啦!和平啦!解放啦!”
“自由”、“解放”成為這一伙人響亮的口號,但他們決不是在那里為處在下層社會的羅馬全體公民而歡呼,更不可能為被剝奪了人格和人身自由、遭受沉重壓迫的奴隸們伸張正義。有一個很鮮明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貴族集團對于廣大的羅馬人民的政治態(tài)度。
愷撒曾當眾三次拒絕了安東尼的勸進,把獻上的王冠擋了回去,且聽聽凱斯卡(小集團的一員)這樣形容羅馬公民的熱烈反應(yīng)吧:
那些烏合之眾高聲狂叫,拍著他們粗糙的手掌,把他們滿是汗臭的睡帽拋向天空,把他們的口臭散布在空氣之中,為的是愷撒拒絕了王冠,結(jié)果差一點兒把愷撒熏死,他暈倒在地上了。至于我,我不敢笑出聲來,惟恐一開口就把那污濁的空氣吸進肺腑。
(第一幕第二景)
語氣之間毫不掩飾他對于人民群眾的極端鄙視的態(tài)度,實際上,這也反映了這一小集團對于群眾的態(tài)度。至于對于被踐踏在社會最底層的奴隸,那就更不必說了。即使對待家仆比較寬厚的勃魯托斯吧,在激烈的爭吵中這樣警告卡修斯:
把滿腔怒火向你的奴隸們發(fā)作吧,
讓他們嚇得發(fā)抖吧。
(第四幕第三景)
那豈不是說:在奴隸面前只管做你作威作福的主子吧,這跟我不相干,可別以為我會忍氣吞聲,像一名奴隸。
卡修斯一聽說元老院明天準備立愷撒為王,當即亮出匕首表態(tài)道:“卡修斯將從奴役下解救出卡修斯。”他的同黨應(yīng)聲道:“每一個被束縛的奴隸,都可以用他們自己的手來掙脫鎖鏈。”(第一幕第三景)多么地慷慨激昂!其實這些動聽的吶喊無非在表明羅馬貴族所享有的傳統(tǒng)的特權(quán)是絕不容侵犯的。至于作為奴隸主的貴族竟會容忍奴隸們當真“掙脫鎖鏈”、解放自己,那是休想了。
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們策劃、密謀、付諸行動的整個過程中,從沒有誰提出過一幅政治藍圖,足以表明他們的宏愿在于為廣大的羅馬群眾爭取民主權(quán)利。倒是暗殺成功,政變者重新安排元老院的新顯貴,試圖拉攏安東尼時,卡修斯的一句話泄露了他們的真意所在:
加入我們志同道合者的行列,還是不愿與我們共事,由我們自行其是?
言下之意,我們可以考慮給你安排一個適當?shù)奈恢谩T瓉硭麄兂魫鹑鲞@眼中釘,實際上是為了好在羅馬貴族集團中進行權(quán)力再分配。
群眾聚集在廣場上,為愷撒的遇難要求得到一個解釋。勃魯托斯發(fā)表一篇措辭漂亮又簡潔的演說詞。他并沒能正面提出他的政治綱領(lǐng),而是反問道:“你們愿意讓愷撒活在世上,大家做奴隸而死呢?還是讓愷撒死去,大家做自由人而生?”(第三幕第二景)
誰自甘墮落、愿意做卑賤的奴隸呢?但是具有極大諷刺意義的是,被鼓動的群眾為勃魯托斯發(fā)出歡呼道:“讓他做‘愷撒’!拿愷撒的榮耀為勃魯托斯加冕吧!”
勃魯托斯以愛國者自居,刺殺愷撒是為民除害,是懲罰他稱霸稱王的野心;可是羅馬的群眾偏要讓勃魯托斯做愷撒第二,仿佛這羅馬大國就是缺少不了一個當家做主、至高至尊的愷撒。最有意思的是“拿愷撒的榮耀為勃魯托斯加冕吧!”勃魯托斯他們竭力維護的是由貴族上層集團統(tǒng)治的岌岌可危的羅馬共和國;而羅馬群眾卻似乎并不在乎誰來統(tǒng)治這個國家:元老院還是愷撒,只要讓他們能過上安安穩(wěn)穩(wěn)的日子。
很明顯,以勃魯托斯為首的這一小集團并沒有群眾基礎(chǔ)。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勃魯托斯的高尚的理想并不為群眾所理解,更不用說為他們能真正接受了。
接著登臺向群眾講話的是一個比勃魯托斯更強的政治活動家,在講壇上更有辯才的鼓動家。安東尼實際上是利用公開的講壇,針鋒相對地和對手展開一場政治大辯論:愷撒究竟是不是“有野心的”暴君?
作為愷撒的追隨者,他知道處境的危險,說話不能不轉(zhuǎn)彎抹角;可是他算準了他手中拿著一副好牌。不像勃魯托斯盡說些不著邊際的漂亮話,他跟群眾一起回憶愷撒生前為國為民所做的一件件好事,就是他打出的一張張牌:愷撒把敵人交納的贖金都充實了國庫;窮苦的人的哭聲讓他流下了淚;他三次當眾拒絕了王冠等等。安東尼攤出來的都是羅馬群眾切身感受、還沒有忘了的具體事實;他們議論開了:“他真的沒有一點野心。”“愷撒死得是很冤枉。”安東尼眼看時機成熟,于是拋出了手中最后一張王牌——宣讀愷撒生前立下的遺囑:給每一個羅馬公民七十五德拉克馬,還捐出私人的產(chǎn)業(yè)作為公共游樂的場所。
安東尼始終一口一聲“勃魯托斯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最后終于變成了無情的挖苦、諷刺,成了射向?qū)Ψ疥嚑I的一枝枝冷箭。群眾得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更愛羅馬的是愷撒,而不是空談著“不是我不愛愷撒,而是我更愛羅馬”的勃魯托斯。他們怒吼了:“他們是叛賊!什么品德高尚的人!”安東尼無異在他們心里放了一把火,他們流下了淚,準備用焚化愷撒的火把去焚燒勃魯托斯的住宅。
劇作家筆下的人物形象在藝術(shù)成就上也值得注意。
愷撒在群眾的歡呼聲中凱旋而返,一出場就聲勢不凡。他說話不多,但每句話都干脆、有分量、切中要害:
看那個卡修斯,一張消瘦、饑餓的臉;
他心眼兒太多,這種人是危險的。
還說“這樣的人只要看到別人高過自己,心里就無法平靜”。他看得很準,用不多幾句話就把一個陰謀家的嘴臉勾勒出來了。接著,他又向身邊的安東尼解釋道:
我只是告訴你,什么人是可怕的,
并非我懼怕他們,因為我永遠是愷撒。
“我永遠是愷撒”,這句話可說擲地有聲,是愷撒的自豪感,或者說,自我崇拜心理的自我表白。對于他,“愷撒”這個顯赫的姓氏已經(jīng)成為至高無上、無所畏懼的統(tǒng)治者的同義詞了。
愷撒說到自己,很少用第一人稱“我”,他更喜歡以充滿尊嚴感的“愷撒”來稱呼自己:
愷撒比“危險”更危險,我們是同一胎
產(chǎn)下的兩頭雄獅;我是老大,
比它更兇猛。
(第二幕第二景)
人家懇求他收回成命,得到的拒絕是:“愷撒是不會有錯誤的。”然而有意思的是,當他宣稱自己誰都不怕,因為“我永遠是愷撒”時,接著卻要他的親信安東尼走到他的右手邊,“因為這只耳朵是聾的”。
他把自己比做天上的北極星,是一位凜然不可侵犯的超人,可是一句話卻泄了底,原來在公眾崇拜的偶像后面,另有一個免不了老弱病殘之苦的凡人。在政敵卡修斯的眼里,偉人的光彩更是完全剝落了:愷撒曾經(jīng)沉溺在水中呼救,曾經(jīng)在軍旅中害了熱病,渾身打戰(zhàn)……
自我崇拜常使愷撒忘了自己也是個凡人,而恰恰在這里,他暴露了一個凡人所免不了的弱點。他的政敵正是看準了他這一弱點而達到了暗殺的目的。愷撒本來已聽從妻子的勸告,答應(yīng)不去羅馬元老院了;卻經(jīng)不起上門來的政客們故意用話刺激他:要是愷撒躲在家里,元老們會怎樣竊竊私議呢?——“瞧,愷撒害怕了!”就憑這句話,雄才大略的愷撒終于被人牽著鼻子走,陷入敵人的包圍圈,成了陰謀的犧牲品。
陰謀家們揮舞著血淋淋的匕首,歡呼道:“暴君死了!”他們常用“暴君”來稱呼愷撒,但是不可一世的愷撒卻得到人民的擁護、愛戴;歷史上并沒有留下他苛政暴行的記載。暴君,應(yīng)是指他破壞了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大權(quán)獨攬,凌駕于羅馬元老院之上,儼然是不戴王冠的統(tǒng)治者。但是公元前40年的羅馬,已不同于公元前五世紀早期的羅馬貴族共和城邦了,它已成為地跨歐、非、亞三洲,把地中海作為自己內(nèi)海的殖民地宗主國了,一個全面協(xié)調(diào)、中央集權(quán)的體制的出現(xiàn),恐怕是遲早之間的事。保守派貴族惟恐愷撒稱帝,先下手為強,實行“宮廷政變”;但是他們并未能阻止事物發(fā)展的趨勢。十七年后,他的侄子屋大維登上元首的寶座(前27年),號稱“奧古斯都”(意為至尊至圣),建立起龐大的羅馬帝國。
另一位悲劇性的主人公是勃魯托斯。“我喜愛光榮的名字,甚于害怕死亡”(第一幕第二景),這可說是他立身處世的座右銘。榮譽感時時刻刻在激勵他、驅(qū)策他;但恰恰是這過分強烈的榮譽感構(gòu)成了他的悲劇性格,別有用心的人在他身上找到了可以利用的弱點。
他光明磊落,眾望所歸;陰謀家們必須爭取他,擁戴他為首領(lǐng),好給他們的所作所為抹上一層道德的保護色彩:
那些在我們似乎是罪惡的事兒,
他一點頭,就像最輝煌的點金術(shù),
轉(zhuǎn)眼成了高尚而仁義的善舉。
(第一幕第三景)
愷撒當眾拒絕勸進,被陰謀家形容為一幕丑劇,這引起了勃魯托斯的憂思:他對愷撒并無個人恩怨,只是為了羅馬,他必須死;倒不是他目前有什么過錯,而是為了鏟除后患;決不能眼看他稱王。與其讓毒蛇從蛇蛋中孵出來傷人,不如趁它還在蛋殼中把它殺死。
恰好陰謀者暗中投來了無頭信,呼吁他:“站出來說話吧,下手吧,為民除害吧!”這一著果然很有效,他當即以羅馬的拯救者自任。卡修斯一伙接著上門來拉攏他了:“這兒的人/沒有誰不尊敬您,沒有哪一個不希望/您多多看重您自己,就像每一個/高貴的羅馬人那樣看重您。”就這樣,勃魯托斯和陰謀家們一一握手為盟,充當了他們的盟主。
這本是策劃中的一場流血的“宮廷政變”,可勃魯托斯從他的榮譽感出發(fā),一開始就把它神圣化了:“我們要做獻祭者,不要做屠夫。”“讓我們被稱作惡勢力的清除者,而不是殺人兇手。”
卡修斯提出,為了免除后患,殺死了愷撒,他的心腹安東尼也得死。勃魯托斯卻要給他們的暗殺活動劃一條道德界線,為安東尼網(wǎng)開一面。安東尼自請接受死罪的處分,勃魯托斯說道:“你只看見我們的手/在行動中沾染了血腥,卻并沒看到/我們的心充滿著憐憫。”
他甚至不顧卡修斯的警告、反對,同意安東尼作為死者的朋友在愷撒的遺體旁向群眾致悼詞。安東尼在口口聲聲稱道勃魯托斯是正人君子的同時,卻讓扮演著獻祭者的“正人君子”終于還原為血腥的叛逆者。他的演說,無異在群眾的心中放了一把火,他們爆發(fā)出一陣陣憤怒的口號:“哦,叛徒!奸賊!”“我們要燒掉勃魯托斯的宅子!”
勃魯托斯他們只能倉皇逃出了羅馬城。借著勃魯托斯的聲譽,那一伙陰謀者為自己豎起了一面大旗,但也正是勃魯托斯的理想主義壞了他們的大事。勃魯托斯的榮譽感使他成為一個悲劇性人物。
意大利爆發(fā)了內(nèi)戰(zhàn)。在營帳內(nèi),勃魯托斯和卡修斯之間爆發(fā)了一場爭吵;但即使爭吵得面紅耳赤,卡修斯并沒有忘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他所結(jié)交的惟一值得尊敬的朋友,只有勃魯托斯的友誼最值得他自豪。勃魯托斯只管咄咄逼人地責問他,他卻只是在招架,在一步步退讓,吐出了他的辛酸話:
即使你最恨愷撒的時候,你愛他
也始終勝過了卡修斯。
他終于屈服,請求原諒,承認母親給了他暴躁的壞脾氣;最后聽說勃魯托斯的愛妻由于丈夫的失敗而自殺了,他獻上了真摯的慰問,充分理解好友這時的痛苦心情。二人為恢復(fù)了友誼而干杯時,他情不自禁地說:“喝著勃魯托斯的友情,我永不知足。”
愷撒形容臉上沒有肉、沒有笑容的卡修斯是個危險人物。我們讀者也不會喜歡他。可是在這一段富于人情味兒的穿插里,劇作家給這個性格陰冷的人物添上了一抹暖色調(diào)——不是一無可取,還多少有他的可取之處。
比起勃魯托斯來,他是更有實際經(jīng)驗、更有應(yīng)變能力的政治活動家。勃魯托斯生活在他的理想中。出于對他的尊敬,卡修斯總是放棄自己的判斷,聽從了他的意見。事后證明,勃魯托斯的每一著都走錯了;可從沒聽說卡修斯向他算倒賬,直到最后,和安東尼對陣、喊話之后,才露出了幾句無奈的埋怨;劇作家又一次讓我們看到這個尖刻的人也有他的人之常情:
你看,勃魯托斯,感謝你自己吧——
要是早聽了我卡修斯的話,
也不會有一條向我們放肆的舌頭了。
(第五幕第一景)
全劇結(jié)束于安東尼在勃魯托斯遺體前所表達的敬意:“這一位是他們中最高貴的羅馬人。”還說只有他,出于正義感才卷進了陰謀小集團。劇作家寫出了他的不可避免的悲劇,并沒有抹殺他在人品道德上自有可敬之處,更可貴的是,他自有一種人格上的魅力,讓人忘了這里是一位遙遠的古代人物。
這一古羅馬悲劇寫的是男性占統(tǒng)治地位的政治舞臺。這里是男人們的天下,沒有女人插足、說話的余地。因此全劇只有兩個女角,她們的戲又少;勃魯托斯的愛妻只是在一場戲中露了臉,給人留下的印象卻是難忘的。她沒有可能提出婦女的社會地位,卻以愛情的名義堅持婦女在她的小天地里,也即在她的家庭里,應(yīng)該享有和丈夫平起平坐的地位。這確是一位值得欽佩的古代婦女,已在《錯盡錯絕》、《奧瑟羅》的前言中有所論及,這里從略了。
方平
注釋:
[1] 在英國清教徒克倫威爾統(tǒng)治下,英國曾有過短暫的共和政體時期(1649~1660),但那已是在莎士比亞逝世三四十年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