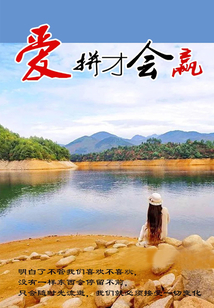
愛(ài)拼才會(huì)贏
最新章節(jié)
- 第6章 充滿希望,樹(shù)立信心
- 第5章 快樂(lè)心理學(xué)
- 第4章 心中有愛(ài)天地寬
- 第3章 挫折心理學(xué)
- 第2章 好思路是一種境界
- 第1章 人生價(jià)值的本質(zhì)
第1章 人生價(jià)值的本質(zhì)
認(rèn)識(shí)你自己
雅典德?tīng)柗粕駨R前的石碑上鐫刻著阿波羅的神諭:人啊,你要認(rèn)識(shí)你自己!埃及法老、釋迦牟尼、蘇格拉底、耶穌、穆罕默德、孔老孟莊等圣人先知無(wú)一不在吶喊:人,要認(rèn)識(shí)你自己!
人是宇宙的奧秘。認(rèn)識(shí)人是最難的。悲劇,迄今仍是人類個(gè)體的宿命。迄今為止,“人”,仍然是個(gè)謎。和“人是什么”這個(gè)問(wèn)題一樣,追問(wèn)人生的價(jià)值同樣是一個(gè)非常困難的問(wèn)題。理性主義的哲學(xué)觀認(rèn)為,世界是一個(gè)有規(guī)律、有邏輯、有價(jià)值的客觀存在;人是宇宙的精華,可以認(rèn)識(shí)自己,認(rèn)識(shí)世界,戰(zhàn)勝自然。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莫不如是。然而,伴隨著工業(yè)文明的到來(lái)以及人類認(rèn)識(shí)的進(jìn)步,對(duì)理性主義的打擊也紛至沓來(lái)——首先是哥白尼的日心說(shuō),發(fā)現(xiàn)主宰世界的人原只不過(guò)是茫茫宇宙中一顆小行星上的塵埃;接著是達(dá)爾文的進(jìn)化論,宣布人并非是由上帝造的,而是由猴子演變進(jìn)化而來(lái);繼之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xué)說(shuō),聲明人連自己都認(rèn)識(shí)不了,主宰不了……三次沉重的打擊之下,營(yíng)造了千年的理性主義大廈轟然倒塌,令人目瞪口呆,驚心動(dòng)魄。叔本華、尼采、薩特等人進(jìn)一步提出了荒謬哲學(xué),認(rèn)為人的存在并沒(méi)有合理性,價(jià)值只是選擇的結(jié)果。
價(jià)值是選擇的結(jié)果!但這種結(jié)論并沒(méi)有正面回答“人是什么”和“人生的價(jià)值是什么”這兩個(gè)問(wèn)題,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種努力的方向。只要人類存在,這兩個(gè)問(wèn)題也許將會(huì)永遠(yuǎn)被追問(wèn)下去,人還是需要認(rèn)識(shí)自己、追問(wèn)自身價(jià)值。在所有的智慧形態(tài)中,認(rèn)識(shí)自我的智慧排在最后。然而,從某種價(jià)值上說(shuō),這也是最重要的一種智慧。這種智慧決定了一個(gè)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如何面對(duì)生命。有多少人為了提高自己的表達(dá)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不惜花費(fèi)時(shí)間和重金,可是大多數(shù)人在探究真實(shí)的自我時(shí)卻裹足不前。
也許你是一位成功人士,事業(yè)有成,家庭幸福。可是有一天,一陣莫名的空虛突然侵襲了你,你突然感覺(jué)自己無(wú)所依傍,從前所追求的一切突然都失去了價(jià)值。你忍不住問(wèn):“我到底怎么了?”
也許你一直平平淡淡,毫不引人注目,平庸麻木的生活早已消磨掉你的銳氣和志向。然而,當(dāng)你看到那些成功人士時(shí),仍然會(huì)心存茫然。你會(huì)忍不住問(wèn):“我到底怎么了?”正是對(duì)于“自我”的追尋,才能使你撥云見(jiàn)日,看到真正的自我,使生活充滿價(jià)值。當(dāng)這種動(dòng)力足夠大時(shí),甚至?xí)淖兡愕囊簧?
人生如流
據(jù)說(shuō),孔子去郊游,他站在河邊,看到下面的流水說(shuō):“過(guò)去的就像這下面的流水一樣,白天晚上都在流。”
這兩句話的文學(xué)氣息非常重,又最富于哲學(xué)意味。佛家也說(shuō)過(guò)水,我們看到流水,永遠(yuǎn)只是一股流水而已。按照佛學(xué)的分析,人的心理就和流水一樣,如說(shuō)“滾滾長(zhǎng)江東逝水”,永遠(yuǎn)在流,真的嗎?錯(cuò)了。這等于看到電燈光,說(shuō)它一直亮著,也錯(cuò)了。當(dāng)我們看到一個(gè)浪頭的時(shí)候,事實(shí)上這個(gè)浪頭已經(jīng)過(guò)去了,是接上來(lái)的另一個(gè)新浪頭,當(dāng)在看到這新的第二個(gè)浪頭時(shí),它又已經(jīng)過(guò)去了。燈光也是一樣,當(dāng)我們剛一打開(kāi)開(kāi)關(guān)時(shí),所發(fā)出的光波已經(jīng)消失了。
我們的思想、感覺(jué)、年齡、身體,當(dāng)1個(gè)鐘頭乃至1分鐘前坐在這里的我,與此刻坐在這里的我,已經(jīng)不知道經(jīng)過(guò)多少變化了。所以“今我非故我”,現(xiàn)在的我已經(jīng)不是前1分鐘的我了。一切都過(guò)去了,像流水一樣,不斷地向前去。
所謂“江水東流去不回”,歷史永遠(yuǎn)不會(huì)回頭,時(shí)間永遠(yuǎn)不會(huì)回頭。人生永遠(yuǎn)像浪頭一樣,一波又一波地過(guò)去了,要想拉回來(lái)是做不到的。我們也許都知道《紅樓夢(mèng)》中林黛玉葬花的故事。弱不禁風(fēng)的她把落花收回來(lái),然后葬下去,情調(diào)非常美,她還作了首好文章,《葬花詞》有句名句:“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shuí)?”
清代文人龔定庵的詩(shī)就比林黛玉高明樂(lè)觀得多,他的詩(shī)說(shuō):“落紅不是無(wú)情物,化作春泥更護(hù)花。”
但是,不管是林黛玉還是龔定庵都是從悲觀的角度來(lái)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孔子并沒(méi)有以悲觀的態(tài)度來(lái)說(shuō)這句話,他是從另一面,用積極的觀點(diǎn)來(lái)看人生。人生如流水一樣,不斷地向前涌進(jìn)。
人生就像這股流水一樣。孔子所以站在上流告訴學(xué)生們:“注意呀!你們看這水,過(guò)去的都像這樣,向前面去!向前面去!而且是晝夜不停地向前去。”
他這話的意義,就是我們經(jīng)常看到的一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
人生也是這樣,要不斷求進(jìn)步。靜是緩慢的動(dòng)態(tài),沒(méi)有真正絕對(duì)的靜。譬如人坐在椅子上好像很靜,其實(shí)并不靜,身上的血液正在分秒不停地循環(huán),各個(gè)器官也都各司其職地工作著。
“天行健”是永遠(yuǎn)強(qiáng)健地運(yùn)行。“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是教我們效法宇宙一樣,即如孔子所說(shuō)“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斷前進(jìn),也就是《大學(xué)》這部書(shū)中所說(shuō)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觀念,都要不斷地進(jìn)步。滿足于今日的成就,即是落伍。所以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句話,包括各方面很多意義,可以說(shuō)孔子的哲學(xué),尤其人生哲學(xué)的精華,都集中在這兩句話中,它可以從消極的、積極的各方面看,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
總之,歷史是不能停留的,時(shí)代是向前邁進(jìn)的,宇宙如此,人生也是如此,關(guān)鍵在于我們用積極還是悲觀的態(tài)度去看待。
人的獨(dú)特性
舍勒在其一生最后的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坦率直言:“從我的哲學(xué)意識(shí)第一次覺(jué)醒的時(shí)刻起,‘人是什么以及他在宇宙中占有什么地位’這個(gè)問(wèn)題,就比其他任何哲學(xué)問(wèn)題,在我心中占有更深刻的、更為中心的位置。”顯然,人是什么的問(wèn)題是一個(gè)亙古至今的永恒的問(wèn)題,從古希臘蘇格拉底明確提出“認(rèn)識(shí)你自己”的口號(hào)起,西方哲學(xué)的研究中心開(kāi)始從天上回到人間,但在一個(gè)漫長(zhǎng)的時(shí)期,西方哲學(xué)對(duì)人的界定由于理性主義長(zhǎng)期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也始終囿于“人是理性的動(dòng)物”的范圍。直到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當(dāng)叔本華、尼采等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對(duì)人的界定才擺脫了理性的框架,從人的意志、欲望、本能等探討人的本質(zhì)在20世紀(jì)成為一種主導(dǎo)方向。對(duì)此,舍勒指出,傳統(tǒng)哲學(xué)將人歸于理性或精神,現(xiàn)代哲學(xué)將人歸結(jié)為生命的本能沖動(dòng)等,兩者都是各執(zhí)一端,失之偏頗。
舍勒指出:“生命和精神相互補(bǔ)充,而過(guò)去的一個(gè)主要誤解是把它們看作原來(lái)就是對(duì)立、斗爭(zhēng)的狀況。”而人卻是生命沖動(dòng)和精神的統(tǒng)一,因?yàn)椤吧鼪_動(dòng)和精神是人的不可分離的兩個(gè)方面。缺乏精神的人不是現(xiàn)實(shí)的個(gè)人,他無(wú)法把自己同地位區(qū)分開(kāi)。沒(méi)有生命沖動(dòng)的人不是實(shí)在的人,而是鬼怪或幽靈。作為一個(gè)完整的人必須同時(shí)兼生命沖動(dòng)和精神于一身,融激情與理智于一爐。人既是生命沖動(dòng)的體現(xiàn),又是精神活動(dòng)的場(chǎng)所,人是生命沖動(dòng)與精神之間的張力和運(yùn)動(dòng)的中介,他不棲居于某一邊”;因?yàn)樯鼪_動(dòng)是人的本能,既具有生命最直接和最基礎(chǔ)的強(qiáng)大力量,又存在著原始的、盲目的、易受本能與欲望支配無(wú)所顧忌的特點(diǎn),因此,需要通過(guò)理性或精神的引導(dǎo),使人生不至于由本能沖動(dòng)信馬由韁,而是引導(dǎo)生命沖動(dòng)實(shí)現(xiàn)精神和價(jià)值的目標(biāo);因?yàn)榫竦淖非笫侨松赜械木辰纾侨嗽谧匀蝗f(wàn)物中享有尊嚴(yán)與高貴所在,它是在人的生命的展開(kāi)過(guò)程中不斷豐富與發(fā)展的,因此,它需要從生命的沖動(dòng)中汲取源源不斷的力量、激情與欲望,擁有生命的不斷持久的動(dòng)力,推動(dòng)精神追求的不斷豐富與完美深邃。
正是因?yàn)樯途竦膶?duì)立與統(tǒng)一,構(gòu)成了一種推動(dòng)人生不斷發(fā)展的力量之源,人成為生命與精神相統(tǒng)一的存在;人生也由此呈現(xiàn)出“生命精神化”與“精神生命化”相并存的存在與展開(kāi)。
舍勒在回答了人是什么的問(wèn)題之后,又把關(guān)注點(diǎn)聚焦于對(du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wèn)題的探討,他認(rèn)為人在宇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擁有獨(dú)一無(wú)二性。
從人與動(dòng)物的比較來(lái)看,人是一個(gè)能向世界無(wú)限開(kāi)放的存在。舍勒認(rèn)為“動(dòng)物的任何行為都來(lái)源于動(dòng)物的某種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狀態(tài)。它們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在心理范圍受本能的沖動(dòng)所支配,為感覺(jué)、知覺(jué)所操縱。對(duì)動(dòng)物來(lái)說(shuō),主要引起它們的生物心理興趣的東西才是它們的對(duì)象和環(huán)境,才是它們所屬的世界。而人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不單純依賴于他的物理和心理狀態(tài),不僅僅依賴于他的本能與環(huán)境。人是以精神為本質(zhì)、以生命為基礎(chǔ)同環(huán)境世界發(fā)生關(guān)系的。人通過(guò)精神抑制或調(diào)節(jié)欲望和本能,人借助理性、直觀、體驗(yàn)、意志、情感以及價(jià)值能力來(lái)與周圍世界發(fā)生關(guān)系,這種人與世界的特殊關(guān)系打破了那種動(dòng)物和環(huán)境的狹隘封閉性,構(gòu)成了人向世界的開(kāi)放性。”
顯然,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舍勒的思想一方面是承繼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tǒng),即在人與動(dòng)物相比較的時(shí)候,人以理性優(yōu)于動(dòng)物;另一方面,也與現(xiàn)代西方人本主義思潮對(duì)人的本質(zhì)的看法相似,即人與動(dòng)物相比,人的本質(zhì)不是固定的,在叔本華、尼采那兒強(qiáng)調(diào)的是生存意志、強(qiáng)力意志決定生命發(fā)展的強(qiáng)弱;在海德格爾那里是以人的“此在”特點(diǎn)凸顯人和其他所有一切存在者的不同,人不是現(xiàn)成既定的存在者,而總是處在未定之中,是“此在”,“此在”的特點(diǎn)是其所尚不是而將足的存在,所以他總是不斷策劃、設(shè)計(jì)、選擇和超越自己,從而獲得自己的本質(zhì)。而薩特則認(rèn)為人的“存在先于本質(zhì)”,人與萬(wàn)物相比,人的本質(zhì)不是被設(shè)定好的,而是人自己所造就的。這些人本主義哲學(xué)家的觀點(diǎn)雖然視角不同,但思想中皆反映了人是一種開(kāi)放性的存在。舍勒的思想在強(qiáng)調(diào)人是生命沖動(dòng)與精神相統(tǒng)一的基礎(chǔ)上,以精神之作用,突出了人的生命在宇宙萬(wàn)物中的獨(dú)具的開(kāi)放性的性質(zhì),“這種關(guān)系表明人按其本性來(lái)說(shuō),本質(zhì)上是能夠無(wú)限地?cái)U(kuò)張到他自己作用范圍的地方——擴(kuò)展到現(xiàn)存世界所能延伸到的地方。人是一個(gè)能夠向世界無(wú)限開(kāi)放的X。”顯然,是人的精神的能動(dòng)性成就了人的無(wú)限開(kāi)放性,是人的主體性凸顯了人與動(dòng)物相比的獨(dú)特性。
從人與歷史的關(guān)系來(lái)看,舍勒“關(guān)于人的生命精神化和精神生命化導(dǎo)致了他對(duì)歷史新的理解。歷史既是生命沖動(dòng)的歷史,又是精神發(fā)展的歷史,但不是一個(gè)統(tǒng)治,另一個(gè)被統(tǒng)治。兩者的依賴與合作產(chǎn)生了歷史。生命沖動(dòng)在歷史發(fā)展中起動(dòng)力作用。人的欲望、本能和激情在歷史發(fā)展中有著巨大的作用,生命沖動(dòng)在歷史上曾引起了經(jīng)濟(jì)的、政治的和種族的發(fā)展。”顯然,舍勒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欲望、生命存在的本能需要對(duì)于人的存在及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重要作用,但同時(shí)他也看到人的精神對(duì)于歷史的巨大影響,“人的精神為歷史發(fā)展提供了一個(gè)無(wú)限開(kāi)放的可能性。由于精神的變化性,使歷史的發(fā)展沒(méi)有預(yù)定的目標(biāo)和先在的計(jì)劃;由于精神的多樣性,決定了歷史發(fā)展的多元化;由于精神的開(kāi)放性,導(dǎo)致了歷史發(fā)展呈現(xiàn)出無(wú)限豐富、多樣而又復(fù)雜的發(fā)展樣式。精神引導(dǎo)歷史由低向高的發(fā)展,但這種發(fā)展又是通過(guò)隨機(jī)和偶然實(shí)現(xiàn)的。正是在這個(gè)價(jià)值上,舍勒認(rèn)為,歷史發(fā)展的結(jié)構(gòu)本質(zhì)上是精神的結(jié)構(gòu)。”這樣,通過(guò)生命沖動(dòng)與精神的能動(dòng)性,人類的歷史呈現(xiàn)出既有生命本能為依托,又有精神價(jià)值為指引的無(wú)限發(fā)展與豐富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人在宇宙中的獨(dú)特性又一次展示出來(lái)。
人的每一個(gè)瞬間都是變易的
人是如何存在的呢?現(xiàn)代法國(guó)哲學(xué)家柏格森認(rèn)為,人是在時(shí)間的綿延中存在著的。如真實(shí)的時(shí)間并不能分割為瞬間一樣,人的真實(shí)存在也是不能分解的。我們?nèi)粘A?xí)慣上將人的生存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如少年、青年、老年等等,這只是用來(lái)滿足人類理性認(rèn)識(shí)的需要,就像物理學(xué)中通過(guò)時(shí)間刻度來(lái)研究物體在某一時(shí)間的運(yùn)動(dòng)狀態(tài)一樣,人需要依據(jù)精確的時(shí)間階段從外部研究、認(rèn)識(shí)人的存在,但這種認(rèn)識(shí)并不能達(dá)到人的存在的真諦。人的存在是一種生命的流動(dòng),無(wú)時(shí)無(wú)刻都在生成著、變化著,只是當(dāng)其變化得足夠充分、完全時(shí),才會(huì)引起人的存在的外在表現(xiàn)的改變,于是我們才觀察到人的生存從一個(gè)階段飛躍到另一個(gè)階段。人的存在就是永恒的流變,其本質(zhì)是什么?對(duì)有意識(shí)的存在者來(lái)說(shuō),存在就是變易;變易就是成熟;成熟就是無(wú)限的自我創(chuàng)造。人生的每一個(gè)瞬間都是變易的,創(chuàng)造的。柏格森從人的存在的兩個(gè)顯而易見(jiàn)的方面給予解釋說(shuō)明,一是人的意識(shí)活動(dòng),二是人的實(shí)踐活動(dòng),柏格森稱其為“生存性活動(dòng)”。
從人的意識(shí)活動(dòng)來(lái)看,人的心理、意識(shí)活動(dòng)等從表面上來(lái)看是彼此分離的,是突發(fā)的。譬如面對(duì)如畫(huà)美景的心曠神怡,挫折沮喪時(shí)的黯然神傷,但其實(shí)這些心理和意識(shí)活動(dòng)卻是以連續(xù)性為基礎(chǔ)的:心曠神怡是因?yàn)楣雌鹦牡椎哪硞€(gè)美好回憶,黯然神傷也可能是因?yàn)橛|及到意識(shí)深處的某個(gè)傷痛。因而,過(guò)去的并未消失,它們?nèi)砸圆煌男问蕉悴卦谝庾R(shí)的某個(gè)角落,并暗自凝聚在現(xiàn)在的力量身邊,與現(xiàn)在融為一體。而現(xiàn)在則是由源源不斷的過(guò)去涌現(xiàn)而成,因此,“當(dāng)我們把自身的存在放回到自己的意志中,并把意志放回到使它綿延的沖動(dòng)中的時(shí)候,我們就可以理解和感受到實(shí)體就是持續(xù)不斷的生長(zhǎng),永無(wú)止境的創(chuàng)造。”從人的“生存性活動(dòng)”來(lái)看,人類實(shí)踐過(guò)程是按照原有的計(jì)劃逐步實(shí)現(xiàn)預(yù)定目標(biāo)的過(guò)程,人的每一項(xiàng)活動(dòng)都包含著創(chuàng)造,都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展現(xiàn),其在本質(zhì)上就是制作活動(dòng)。人類因?yàn)樘幱谟袡C(jī)界進(jìn)化的最高層,并不具備完全適應(yīng)自然環(huán)境的器官,必須在人類意識(shí)的指導(dǎo)下,借助外物來(lái)延長(zhǎng)自己的器官以適應(yīng)生存環(huán)境。人類的制造活動(dòng)開(kāi)始于制造工具,后逐漸又發(fā)展出制造非工具的物質(zhì)來(lái)滿足人類自身日益豐富、復(fù)雜的需要,這種制造活動(dòng)就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斷地經(jīng)歷著生成、創(chuàng)造的意識(shí)活動(dòng)和“生存性活動(dòng)”,人的存在也就是一個(gè)生成的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
由于人是時(shí)間性的存在,時(shí)間所具有的特性也就因此被賦予人的存在,如綿延、流變、無(wú)方向性等。據(jù)此,柏格森認(rèn)為人的生成、創(chuàng)造過(guò)程具有:
一是非終極性。“生命的特性永遠(yuǎn)處于實(shí)現(xiàn)之中,絕不會(huì)完全實(shí)現(xiàn)。在生命進(jìn)化的前方,未來(lái)的大門一直敞開(kāi)著,生命進(jìn)化實(shí)質(zhì)上是起始運(yùn)動(dòng)永不停息的創(chuàng)造。”時(shí)間是一股既無(wú)開(kāi)端也無(wú)終結(jié)的流,它生生不息地向前流逝。時(shí)間性存在的人同樣也既無(wú)開(kāi)始又無(wú)結(jié)束,從無(wú)止境的時(shí)間流動(dòng)中生成、創(chuàng)造。人是以未來(lái)為指向的存在物,人的生成與創(chuàng)造都是向未來(lái)的孜孜不倦地追求,但人的現(xiàn)實(shí)存在又使得人不可能實(shí)現(xiàn)這種追求,人的一生就處于“在路上”的狀態(tài)中,人只可能接近目標(biāo)而無(wú)法達(dá)到目標(biāo)。
由于在個(gè)人、自然、社會(huì)三個(gè)層面的因素對(duì)人的生成、創(chuàng)造的“羈絆”,人不能達(dá)到最終的目標(biāo)。從個(gè)體來(lái)說(shuō),個(gè)人存在的特征在于其個(gè)體性,但個(gè)體又不可能脫離他人、他物而存在,“可見(jiàn)個(gè)體性內(nèi)部就包含著否定的因素,個(gè)體性要求從時(shí)間上得到永存,這反而使它在空間上難以完成”。從自然的層面來(lái)看,人的存在離不開(kāi)物質(zhì),人和物質(zhì)分屬于有機(jī)界和無(wú)機(jī)界,它們運(yùn)動(dòng)的方向是截然相反的,因而人的生成、創(chuàng)造過(guò)程也就必然受到物質(zhì)的阻礙。站在社會(huì)的視角而言,人存在的阻力來(lái)自于人自身,即人的自由與習(xí)慣之間的“拉鋸戰(zhàn)”。柏格森的自由是與生成、創(chuàng)造同等程度的概念,人的真實(shí)的存在不僅是生成、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也是自由得以展現(xiàn)的過(guò)程,因而人對(duì)自由是沒(méi)有選擇權(quán)的。自由似乎已然成為人的一種本性,一種本然的存在狀態(tài),但自由在自我運(yùn)動(dòng)中卻創(chuàng)造出了它的對(duì)立物——習(xí)慣。“我們的自由在確立自由的運(yùn)動(dòng)中創(chuàng)造出日益強(qiáng)大的習(xí)慣勢(shì)力,如果自由不用不懈的努力更新自己,就會(huì)被這些勢(shì)力所窒息,自由后面就是無(wú)意識(shí)。最充滿生機(jī)的思想一經(jīng)公式表達(dá)出來(lái)就變得死板僵滯。語(yǔ)言常常違背思維,文字往往扼殺精神。火熱的激情一旦表現(xiàn)為行動(dòng),就會(huì)自然而然凝固成利益或虛榮的冰冷的數(shù)據(jù)。如果我們不懂得僵死的東西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會(huì)保持活生生事物的特征,當(dāng)一種事物以另一種事物的面貌出現(xiàn)時(shí),我們就會(huì)把它們混為一談,甚至懷疑自己的真誠(chéng)、善良和愛(ài)心。”人的存在就在這無(wú)止境的作用與反作用中生成著,創(chuàng)造著,向那個(gè)不可能達(dá)到的目標(biāo)努力著。
二是不可預(yù)測(cè)性。柏格森認(rèn)為時(shí)間的每一瞬間都發(fā)生著飛躍與質(zhì)變,我們永遠(yuǎn)也把握不住在下一個(gè)瞬間它會(huì)向哪個(gè)方向躍進(jìn),它會(huì)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因而任何理性、知性都無(wú)法認(rèn)識(shí)時(shí)間的真實(shí)存在,只有將自身與時(shí)間的存在狀態(tài)融為一體,用自覺(jué)去體驗(yàn)才能感受到時(shí)間的脈搏。人的存在也是如此,可以預(yù)測(cè)的東西肯定是已經(jīng)被包含在某些已知的經(jīng)驗(yàn)或知識(shí)中了。我們所預(yù)測(cè)出的未來(lái)只是對(duì)已知的推論,并沒(méi)有增添任何新的內(nèi)容,也就不是一個(gè)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自然也就無(wú)法成為人的真實(shí)的存在狀態(tài)的描述。
三是無(wú)方向性。正如柏格森在闡述自己時(shí)間觀時(shí)否定了未來(lái)的真實(shí)性一樣,他認(rèn)為生命是一股無(wú)目的、無(wú)方向的沖動(dòng)、變異,飛躍、流變就是它全部的表現(xiàn)。因此,人生的道路是走出來(lái)的,并無(wú)一個(gè)預(yù)先的“藍(lán)圖”或“方向”,對(duì)于人生的生成與創(chuàng)造,我們所知的僅僅是它生成著,發(fā)展著。基于以上理解,柏格森明確提出:“我們是自己生活的創(chuàng)造者,每一瞬間都是一種創(chuàng)造……因此,完全有理由說(shuō),我們做什么取決于我們是什么。但要附加一句:在某種程度上說(shuō),我是自己行動(dòng)的創(chuàng)造者,我們不斷地創(chuàng)造自己。”柏格森在論述人的生成的非終極性時(shí)已經(jīng)揭示出人存在的一個(gè)矛盾:人既是個(gè)體性的存在,也離不開(kāi)外界的環(huán)境,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人造的環(huán)境(我們通常所說(shuō)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因而人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活不僅僅是創(chuàng)造自己的個(gè)體性,也是創(chuàng)造人所生存的環(huán)境的過(guò)程。
生命由“八苦”構(gòu)成
據(jù)傳,佛祖釋迦牟尼在做迦毗羅衛(wèi)國(guó)王子的時(shí)候,本來(lái)是無(wú)憂無(wú)慮,充滿歡樂(lè)的。釋迦牟尼出身王族,作為太子他生活富貴,這在常人看來(lái),自是幸福至極。然而佛祖卻自幼喜歡沉思,世間的許多現(xiàn)象被他看到之后,都容易引他的感觸和思索。
隨著年齡的增長(zhǎng),宮廷的豪華與享樂(lè)始終未能引起王子的興趣,反而引起他更深的思考:這種富貴的生活是不是人真正應(yīng)該追求的?人世間有諸多的痛苦與不幸,一味追求享樂(lè)就能超脫嗎?耽于此的無(wú)聊消遣,難道不是對(duì)生命的揮霍和浪費(fèi)嗎?怎樣才是符合人本性的生活?他決定要出宮去嘗試探求這一問(wèn)題的答案。
王子第一次走的是城東門。在這里他發(fā)現(xiàn)一個(gè)滿頭白發(fā)的老人,拄著拐杖,弓腰駝背,步履蹣跚。太子問(wèn)隨從:“這是什么人?”隨從回答說(shuō):“老人。”太子就問(wèn):“那什么是老呢?”隨從回答:“人自幼年到童年再到成年,然后就是老年了。這時(shí),容顏衰,氣力變?nèi)酰磺卸疾蝗鐝那傲耍瑢?shí)際上已經(jīng)到了生命的盡頭,就和夕陽(yáng)落山、蠟燭燃盡一樣。”太子又問(wèn):“是不是萬(wàn)物都是如此呢?”隨從回答說(shuō):“一切生命都是如此,都是從盛到衰。”王子心中一陣傷感:時(shí)間使人脆弱不堪,人世的短暫、虛浮使人痛苦而無(wú)奈,人又該怎樣解脫呢?困惑的王子悶悶不樂(lè),無(wú)心出游,回到了王宮。
王子第二次出游走的是南門。剛走出城南門,王子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gè)病人,瘦得皮包骨頭,不停地喘氣呻吟,看樣子快挺不住了。王子問(wèn)隨從:“這是什么人?”隨從回答說(shuō):“這是病人。”王子又問(wèn):“什么是病?”隨從說(shuō):“所謂病,就是人的欲望太甚,身體不調(diào)。人一旦得病,就會(huì)感到難受、不舒服和痛苦,想吃而不能,想動(dòng)而不得。”王子聽(tīng)罷,心中不禁暗生慈悲之情。他又問(wèn)隨從是不是人人都會(huì)得病?得到的回答是人人都會(huì)生病,不論貴賤,不論男女。王子又感到一陣悲傷:人人都逃脫不了疾病的困擾,人活著還有什么意義?又如何解脫呢?恐懼的王子下令回宮。
王子第三次出游走的是西門。在西門,他碰見(jiàn)一群出殯的人,有人抬棺,有人哭泣。這凄慘的場(chǎng)面使王子困惑不解。他問(wèn)隨從:“抬的是什么人?”隨從答說(shuō):“是死人。”他追問(wèn):“什么是死?”隨從告訴他:“死就是肉體沒(méi)了知覺(jué),人一死,世間的事再與他無(wú)關(guān),他所積累的財(cái)富對(duì)他也毫無(wú)用處了。”王子不禁心驚,問(wèn)隨從:“是一人有死,還是人人有死?”得到的回答是:“人人有死,概莫能外。”王子再次感到了恐懼與感傷:人世間苦難何其多,又該如何面對(duì)呢?
經(jīng)過(guò)這三次出游,王子想了許多。既然人人都要面對(duì)老、病、死,人生多夢(mèng),如夢(mèng)如幻,令人傷感,眾生卻不明俗世之虛幻不實(shí),盲目追逐感官欲望的歡樂(lè),真是執(zhí)迷不悟。王子苦苦思索著解脫之道。
王子第四次出游走的是北門。他到了一片樹(shù)林中,天氣晴好,陽(yáng)光燦爛。這時(shí),正在樹(shù)下思考的王子看見(jiàn)一位老僧走了過(guò)來(lái)。在兩人的攀談中,老僧告訴王子,只有斷絕塵世,隱于世外,消解俗欲,方能擺脫現(xiàn)象,心與天通,不受老、病、死的煩擾。王子于是豁然開(kāi)朗,終于走上苦行之路,并最終在菩提樹(shù)下,一連七天七夜,凝神聚思,終于豁然醒悟:人生猶如一個(gè)無(wú)邊無(wú)際的苦海,苦海無(wú)邊,苦就是人生的真實(shí)本相。最終釋迦牟尼悟道成佛。
對(duì)人生具體苦相的劃分,佛家有三苦、八苦之說(shuō),最通常的提法是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huì)苦、愛(ài)別離苦、求不得苦、五蘊(yùn)苦,苦就是人生的真實(shí)本相。
生苦:是指人出生和生存的痛苦。人的出生,要經(jīng)歷十月懷胎,胎兒居住在窄小的子宮內(nèi),猶如關(guān)在黑暗的地獄里,飽受擠壓之苦,胎兒位處腸臟膀胱邊,深受膿血屎溺熏蒸之苦;嬰兒初生之際,肌膚幼嫩,寒風(fēng)觸身,猶如刀刮;長(zhǎng)大之后,人的貧富貴賤,強(qiáng)弱美丑,種種不同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條件和主觀條件,都可以使人產(chǎn)生生存的痛苦。
老苦:人至老年,“頭白齒落,五官失靈”,神智昏暗,肌肉萎縮,四肢乏力,生命不長(zhǎng),死亡將至,實(shí)在令人痛苦。
病苦:佛教所指的病分身病和心病兩種。身病是因?yàn)椤八拇蟛徽{(diào)”而引起的,如“地大”不調(diào),身體僵硬沉重;“水大”不調(diào),身體虛浮腫胖;“火大”不調(diào),人遍體蒸熱高燒;“風(fēng)大”不調(diào),渾身性躁不安。人的身體從頭到腳,從里到外,都會(huì)受到病痛困擾,心病則是因?yàn)槭艿缴钪械母鞣N逼迫而產(chǎn)生的焦慮煩惱和各種憂思悲傷,也使人心力交瘁,痛苦不堪。
死苦:死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人的生命無(wú)常,壽盡終有一死,但更痛苦的是,人還會(huì)因各種意外事故而夭折,如因疾病纏身而死,因遭水火刀兵之害而死,因心靈極度痛苦而死。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死。
怨憎會(huì)苦:在社會(huì)生活中,每個(gè)人都有自己不喜歡乃至憎惡、仇恨的人,都想離這些人遠(yuǎn)遠(yuǎn)的,永遠(yuǎn)不要見(jiàn)到。但人生偏偏是冤家路窄,不愿意看到的人卻往往會(huì)遇見(jiàn)。使人內(nèi)心極不舒服,這就叫怨憎會(huì)苦。
愛(ài)別離苦:與怨憎會(huì)苦相反,每個(gè)人都有自己喜歡的人,希望常相聚,時(shí)時(shí)親近,如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但到頭來(lái)卻終不免是離多聚少,甚至禍起非常,造成生離死別的莫大痛苦。
求不得苦:人心充滿欲求,充滿向往。世人無(wú)不迷戀和追求一切美好迷人的東西。但人的企盼總是落空,追求總是失敗,愿望總難實(shí)現(xiàn),因而造成莫大的痛苦,欲求愈旺,企盼愈高,求不得的痛苦就愈大。
五蘊(yùn)苦:所謂“五蘊(yùn)”,是指物質(zhì)現(xiàn)象的色和精神現(xiàn)象的受、想、行、識(shí),佛家認(rèn)為人就是由此五蘊(yùn)通過(guò)因緣和合而成,而有了五蘊(yùn)就會(huì)產(chǎn)生各種痛苦,所以五蘊(yùn)苦是各種痛苦的總匯。
佛家的八苦之說(shuō),可謂集人生苦痛之大成。既有生理之痛,又有心理之苦,既有欲求不能滿足的傷心,又有欲避不能的無(wú)奈。以此觀照人生,則人生不啻為一苦難的歷程,人的生命是苦,人的生存也是苦。
毫無(wú)疑問(wèn),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我們每個(gè)人又都有過(guò)這樣那樣的痛苦感受,都有過(guò)因環(huán)境逼迫或希望落空所產(chǎn)生的焦慮與煩惱。但問(wèn)題在于,我們每一個(gè)人又都同時(shí)體驗(yàn)過(guò)快樂(lè),享受過(guò)即使是瞬間的無(wú)憂無(wú)慮。正因?yàn)槿松灿袣g樂(lè),也有輝煌,人們才癡迷于對(duì)歡樂(lè)和輝煌的追求,雖身心處于痛苦境況卻仍念念不忘執(zhí)著于對(duì)人生幸福的向往與追求。
可見(jiàn),人生并非絕對(duì)的沒(méi)有現(xiàn)象意義上的幸福與歡樂(lè),但在佛家看來(lái),那是偶然的、變動(dòng)不居和虛幻的,蕓蕓眾生之所以找不到解脫痛苦和消除煩惱的最終出路,之所以在一次次人生追求中失敗而執(zhí)迷不悟,就在于沒(méi)有明白苦才是真實(shí)的恒在。因此,佛家講人生一切皆苦,是對(duì)人生從根本作出的價(jià)值判斷,是從其必然性、真實(shí)性意義上來(lái)講的,是為了強(qiáng)調(diào)人生所充滿的逼迫性。人生的逼迫性是無(wú)處不在,無(wú)處不有的,絕不會(huì)因個(gè)人條件或社會(huì)環(huán)境、歷史時(shí)代的改變而消除,這是佛家對(duì)人生真諦的哲學(xué)穎悟。
既然如此,當(dāng)我們今天試圖從佛教的人生思想中尋求一點(diǎn)于我們有用的人生啟迪時(shí),就大可不必去深究佛家對(duì)人生是苦的價(jià)值判斷是否絕對(duì)真理,也毋須按圖索驥地用佛經(jīng)所列的種種苦難來(lái)指陳我們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中的各種不足。只要我們了解到,佛家所謂苦,乃是指人生所必然遭遇的精神和生理的逼迫性,而這種逼迫性是恒在的,無(wú)論是人類整體,還是其中的某一階層、群體或個(gè)人,都追求甚至實(shí)現(xiàn)過(guò)一個(gè)個(gè)社會(huì)目標(biāo)或人生目標(biāo),但憂慮和煩惱卻始終如影隨形,無(wú)法消除,這便是人生逼迫性無(wú)處不在,無(wú)時(shí)沒(méi)有的表現(xiàn),則我們或許便可不致因在社會(huì)生活中遭遇困難和挫折而驚慌失措、悲觀失望,便可更為坦然從容地去適應(yīng)自己的人生位置,多做一些實(shí)事,少發(fā)一點(diǎn)牢騷。如果再進(jìn)一步,假如我們從佛家對(duì)人生本相的體察中受到啟迪,做到一開(kāi)始就不那么理想主義地和充滿幻想色彩地看待社會(huì)和人生,看待自己的目標(biāo)和追求,則我們或許便可不致因理想的失落或環(huán)境的逼迫而焦慮迷茫,便可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得更為自由和超然,從而超脫無(wú)邊苦海。
無(wú)盡痛苦和無(wú)聊
在德國(guó)哲學(xué)家看來(lái),整個(gè)人生,它只不過(guò)是盲目的生命意志和沖動(dòng)的表現(xiàn),它由無(wú)盡痛苦和無(wú)聊構(gòu)成的。他為此有過(guò)大量相關(guān)的論述。
“人生好比鐘表機(jī)器似的,上好了發(fā)條就走,而不知為什么要走,每有一個(gè)人誕生了,出世了,就是一個(gè)‘人生的鐘’上好了發(fā)條”。“人生好比一場(chǎng)短夢(mèng),是無(wú)盡自然精神的短夢(mèng),常駐的生命意志的短夢(mèng)”。
“人生只不過(guò)是一幅飄忽的畫(huà)像,被意志的游戲的筆墨畫(huà)在它那無(wú)盡的畫(huà)幅上,畫(huà)在空間和時(shí)間上,讓畫(huà)像短促地停留片刻,和時(shí)間相比,只是近于零的片刻,然后又抹去,以便為新的畫(huà)像空出位來(lái)……”;“人生如灼熱的紅炭所構(gòu)成的圓形軌道,軌道上有幾處陰涼的地方,而我們又必須不停地跑過(guò)這軌道,那么被局限于幻覺(jué)的人就以他正站在這上面的或眼前看得到的陰涼之處安慰自己而繼續(xù)在軌道上往前跑”。
這些生動(dòng)而可怕的比喻,把人生看成是痛苦的淵藪。在叔本華看來(lái),但丁的《煉獄篇》之所以比《天堂篇》寫得真實(shí)成功,就是因?yàn)榈∷鑼懙牡鬲z慘相就是現(xiàn)實(shí)生活苦難的寫照。
在叔本華看來(lái),生命意志的本質(zhì)就是痛苦。而且意志現(xiàn)象愈完善,痛苦也愈多。植物無(wú)痛感,低等動(dòng)物痛感微弱,高等動(dòng)物痛感強(qiáng)烈,人的痛感達(dá)到頂峰。智力愈發(fā)達(dá),痛苦愈多,所以天才最痛苦。正如歌德所講,“天才的命運(yùn)注定是悲劇”。
在他看來(lái),人生好比一個(gè)鐘擺。擺的這端是“痛苦”,而另一端則是“無(wú)聊”。當(dāng)人的欲望沒(méi)得到滿足時(shí),便產(chǎn)生焦慮、痛苦感;而欲望一旦得到滿足,便又會(huì)覺(jué)得“不過(guò)如此”,百無(wú)聊賴,于是又產(chǎn)生新的欲望,尋求新的刺激,重新回到痛苦的欲望中,開(kāi)始新一輪的“鐘擺”生活。
那么,人的本質(zhì)存在為什么就是痛苦呢?或說(shuō),為什么痛苦會(huì)成為人類不可擺脫的命運(yùn)呢?
叔本華說(shu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生而有欲,因?yàn)槿司褪且庵居蟮目陀^化,是“盲目的生命意志和沖動(dòng)的表現(xiàn)”,他說(shuō),作為宇宙本體的意志總是掙扎的,因?yàn)閽暝撬奈ㄒ槐举|(zhì)。
只有受到外部的阻礙,才有可能被暫時(shí)地歇止。你瞧,自然的重力就一個(gè)勁地向一個(gè)無(wú)限廣袤的中心擠去,固態(tài)之物向液態(tài)掙扎,而液態(tài)又向氣態(tài)掙扎。在生物界,到處盛行叢林法則,你死我活,相互吞食的斗爭(zhēng)隨處可見(jiàn)。
至于我們?nèi)祟悾乔О俜N欲求和需要的凝聚體,人帶著這種需要而活在世上,除了自己以外,別無(wú)其他任何依靠,一切都是未定之?dāng)?shù),唯獨(dú)人自己的需要和匱乏是肯定的。據(jù)此,整個(gè)的人生在這樣沉重,在每天開(kāi)門相見(jiàn)的需求之下,一般人都充滿著為了維護(hù)那起碼的生存而生的憂慮。
不僅如此,直接和這憂慮連在一起的又有第二種需求,即種族綿延的需求。同時(shí),各種各樣的危機(jī)又從四面八方威脅著人,他以小心翼翼的步伐,膽戰(zhàn)心驚地向四周環(huán)顧而走著自己艱難的路程,因?yàn)榍О俜N偶然的意外,千百種敵人都在窺伺著他。在荒野里他這樣走著,在文明的社會(huì)里,他也這樣走著。
在叔本華看來(lái),人生就是被無(wú)限的欲求鼓動(dòng)起來(lái)的一葉扁舟,在茫茫的苦海上掙扎。他把人的意志或欲求受到外部的阻礙叫做痛苦,而把意志和欲望的暫時(shí)滿足叫幸福。在人生的大海里航行,也有風(fēng)平浪靜的時(shí)刻,這時(shí)他或許體驗(yàn)到他夢(mèng)寐以求的滿足,稱心如意,或快樂(lè)和幸福,但這只是痛苦的間息期,而決不意味著痛苦的消失,而在兩個(gè)痛苦、即一個(gè)剛消失的痛苦和下一個(gè)即將而來(lái)的痛苦之間息期,并不是被幸福和滿足的感覺(jué)所充實(shí)著,恰恰相反,在一旁窺伺已久的無(wú)聊寂寞之感又迅速乘虛而入。
他說(shuō)“困乏和痛苦如果一旦予人以喘息,空虛無(wú)聊又立即圍攏上來(lái),以致人必然又需要消遣”,這叫做“逃避空虛無(wú)聊的掙扎”。逃避空虛無(wú)聊的掙扎有時(shí)會(huì)使人陷入真正的絕望。
叔本華說(shuō):“空虛無(wú)聊絕不是一件可以輕視的災(zāi)害,到了最后,它會(huì)在人的臉上刻畫(huà)出真正的絕望。它使像人這樣并不怎么互愛(ài)的生物,居然那么急切地相互追求,于是,它又成為人們愛(ài)社交的源泉了。和對(duì)付其他一般災(zāi)害一樣,為了抵制空虛無(wú)聊,單是在政治上的考慮,就到處安排了些公共的設(shè)施,因?yàn)檫@一災(zāi)害和相反的另一極端,即饑餓一樣,都能驅(qū)使人們走向最大限度的肆無(wú)忌憚。‘面包和馬戲’是群眾的需要,匱乏是平民的日常災(zāi)難。空虛無(wú)聊是上層社會(huì)的日常災(zāi)難,在市民社會(huì)中,星期日代表空虛無(wú)聊,六個(gè)工作日則代表困乏。”
總之,人生是在欲求和達(dá)到欲求之間消逝的,欲望在其本質(zhì)上便是痛苦,愿望的達(dá)到又很快產(chǎn)生空虛。目標(biāo)只是如同虛設(shè):占有一物便使一物失去了刺激。于是,愿望、需求又在新的姿態(tài)下卷土重來(lái),要不然,寂寞空虛,無(wú)聊又隨之而起;叔本華對(duì)人生的根本結(jié)論是:“任何人生都是在痛苦和空虛無(wú)聊之間拋來(lái)擲去的。”
叔本華還說(shuō),智力愈發(fā)達(dá),痛苦的程度愈高,因此隨著認(rèn)識(shí)的愈益明確,意識(shí)愈加強(qiáng),痛苦也就增加,這是一個(gè)正比例。到了人,這種痛苦也達(dá)到了最高的程度,并且一個(gè)人的智力愈高,認(rèn)識(shí)愈明確,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則最痛苦。
在我們一般人的觀念中,大抵把痛苦、悲傷、憂慮、畏懼、孤獨(dú)等等看作是人的消極心理體驗(yàn),而把幸福、快樂(lè)、滿足、高興、愉快等等看作是人的積極心理體驗(yàn),但叔本華把這個(gè)提法全部翻了個(gè)個(gè)兒。在他看來(lái),人生的本質(zhì)即在于痛苦和無(wú)聊,那么,當(dāng)他說(shuō):“一切幸福只具有暫時(shí)的、消極的特征”,也是必然的邏輯結(jié)論了。
煩心和麻煩
海德格爾把人的存在看作是人的真正本質(zhì),沒(méi)有了人的存在,其他一切的存在會(huì)變得毫無(wú)價(jià)值。他說(shuō),人的存在優(yōu)先于萬(wàn)物的存在。因?yàn)楹笳咧挥幸揽咳说拇嬖诓拍艿玫秸f(shuō)明。只有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
他認(rèn)為人的存在有兩種基本的特征。其一是人的存在先于本質(zhì);其二人的存在總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
關(guān)于第一個(gè)特征,這是存在主義人生哲學(xué)的第一基本原理。
在以往的哲學(xué)中,大多主張本質(zhì)先于存在,或主張本質(zhì)共存于存在之中。舉個(gè)例子來(lái)說(shuō),圓的本質(zhì)我們可以規(guī)定為“到定點(diǎn)的距離等于定長(zhǎng)的點(diǎn)的軌跡”。圓的這個(gè)本質(zhì)是固定的、普遍的、必然的,而凡具體的圓,如茶杯、輪胎,皮球等等的圓則有生有滅,且越符合圓的本質(zhì)則越圓,于是柏拉圖會(huì)說(shuō),這個(gè)本質(zhì)的圓是具體圓的模本(本質(zhì)先于存在)。
海德格爾把這個(gè)提法倒轉(zhuǎn)了過(guò)來(lái),提出人的存在不同于萬(wàn)物的一個(gè)根本特征,就是存在先于本質(zhì)。他認(rèn)為,對(duì)于桌子、房子、樹(shù),我們可以說(shuō)本質(zhì)先于存在,或本質(zhì)與存在共存。但對(duì)人卻萬(wàn)萬(wàn)不可:人的存在狀態(tài)的一個(gè)根本規(guī)定,就是他的存在,人的本質(zhì)是人通過(guò)自的自由選擇而獲得的。意思是人最初來(lái)到這個(gè)世界時(shí),就是一種存在,人自身的存在,而且這種存在是純粹的、原始的,尚未被規(guī)定的。先有了這種存在,人才塑造自己的本質(zhì),創(chuàng)造自己的價(jià)值,即才給自己以各種各樣的規(guī)定。用薩特的比喻:笛卡爾講“我思故我在”,薩特則反之,“我在故我思”。
存在主義的這一個(gè)觀點(diǎn)直接來(lái)源于尼采。尼采說(shuō),人是未定型的動(dòng)物。因而人能按照自身的意愿創(chuàng)造自己的未來(lái),而動(dòng)物則不能:它們內(nèi)制于本能,外縛于環(huán)境,動(dòng)物是定型了的。因?yàn)樗鼈兪朗来荒苌钤谕画h(huán)境,重復(fù)同一種生活。
海德格爾所謂的人的存在的第二個(gè)特點(diǎn),意思是人的存在總是單個(gè)的人具體的存在,這個(gè)有限的、短暫的生命存在對(duì)于具體的生命所有者來(lái)說(shuō)是“性命攸關(guān)”的東西。海德格爾認(rèn)為,人一經(jīng)卷入這個(gè)喧鬧不息的大眾社會(huì),在追逐外物和輿論聲浪的沉浮中,人把自己最真實(shí)的“存在”或“自我”忘得一干二凈。
海德格爾對(duì)現(xiàn)代大眾社會(huì)中的人的存在狀態(tài)做了診斷:
首先在大眾社會(huì)中,人的個(gè)性消滅了。個(gè)人因無(wú)力對(duì)各類事物作出判斷,然后又要判斷,最方便而安全的方法是遵循“大多數(shù)”人的判斷作為自己的判斷,這樣形成習(xí)慣,結(jié)果把自己僅有的一點(diǎn)判斷能力丟得精光。個(gè)人的獨(dú)立思考和判斷呢?不是忘掉了,而是本來(lái)就沒(méi)有過(guò)。
其次,海德格爾說(shuō),在大眾社會(huì)中,公眾的意見(jiàn)主宰一切,而任何優(yōu)秀的狀態(tài)都被不聲不響地壓住了。其結(jié)果,使得一切不同凡響的、獨(dú)立的、優(yōu)秀的、確有水平的東西都被公眾的不理解而造成的冷漠,或自以為理解而造成的憤怒所壓制。
通常,由于我們自己的懶惰和社會(huì)壓力,我們停留在這樣一個(gè)日常的俗世間,在那里我們并不同我們最內(nèi)在最深層、最重要的自我相接觸。這個(gè)世間是海德格爾稱之為“任何人”或“普通人”的領(lǐng)域,在那里我們是可以彼此替換的,在這個(gè)“人人的領(lǐng)域”里,我們并不意識(shí)到自己的存在。
海德格爾用“沉淪”一詞來(lái)描述個(gè)人的這種存在狀態(tài)。個(gè)人的沉淪與其說(shuō)是由于社會(huì)壓力從外部把個(gè)人拖入到沉淪去,還不如說(shuō)是由于個(gè)人內(nèi)部本身有一種傾向而投入到沉淪中去。因沉淪到眾人中去,與眾人取得一致,可以得到一種“安寧”。如果一個(gè)人獨(dú)立地對(duì)生活做出判斷和決定,他是要由自己承擔(dān)行為后果所帶來(lái)的責(zé)任的;更嚴(yán)重的是,倘若獨(dú)立的決定與眾人有區(qū)別,甚至對(duì)立,他要獨(dú)立地承受來(lái)自四面八方的冷漠和譴責(zé)。所以“沉淪是對(duì)親在(個(gè)人)的一種誘惑”。
海德格爾認(rèn)為,沉淪狀態(tài)有三種展開(kāi)方式,那就是閑談、好奇與兩可。人的共在也就是通過(guò)閑談、好奇和兩可而建立起來(lái)。這就是說(shuō),普通人通過(guò)好奇而取得新奇的消息,通過(guò)閑談而交換意見(jiàn),并通過(guò)兩可而使得各種分歧得到消除,于是他們又歡欣鼓舞地把共同意見(jiàn)作為自己的意見(jiàn)。
人們?cè)谶@種充滿計(jì)謀和傾軋的生存狀態(tài)中所能體驗(yàn)到的一種主要情緒就是“煩”,海德格爾認(rèn)為“煩”是人的基本的存在狀態(tài)。
他認(rèn)為“煩”有兩種形態(tài),即煩心和麻煩。與物打交道時(shí)產(chǎn)生煩心,而與人周旋心生麻煩。他說(shuō):“在麻煩中,人無(wú)論是與他人合謀,還是贊成他人,還是反對(duì)他人,煩總是寄托在此種麻煩中。”
海德格爾認(rèn)為,人沉淪于其中的“煩”的世界,于是處于一種“深閉的狀態(tài)”。只有當(dāng)人受到了重大事件的震動(dòng),并體驗(yàn)到劇烈的苦悶時(shí),這種“深閉狀態(tài)”才能沖破,這時(shí)人的內(nèi)在的自我,或說(shuō)人的最真實(shí)的存在才開(kāi)始向自己的意識(shí)顯示出來(lái)。災(zāi)禍,如嚴(yán)重的疾病、喪親之痛,甚至直接地面臨著死亡,我們就會(huì)被深沉的悲痛和苦悶所包圍,在這樣的時(shí)刻,人就會(huì)意識(shí)到以往在這煩心世界中的一切追求和努力都是徒勞無(wú)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