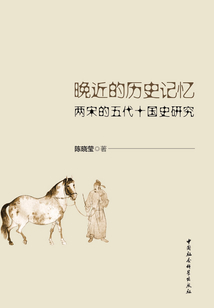
晚近的歷史記憶:兩宋的五代十國史研究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一 研究緣起
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的進一步發展,也是一個“大震蕩、大變革”[1]、“大破壞與大重建之交替時代”[2]。它“亂而后治,治中有亂”[3],“表面上亂,實質是變”[4],于一片大混亂、大混沌當中,開啟了趙宋王朝數百年的太平基業,也奠定了封建社會后期新格局的基礎,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然而,五代十國自古卻是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被認為黑暗混亂,禮義殄滅,文物蕩盡,人才乏力。加之祚運短促,史料匱乏,素來不為史家所重視,視為“最不像樣”[5]的時代。這一印象,正是源自兩宋時朝。
五代十國的歷史于宋人——尤其是北宋——是近代史,這段混亂跌宕的歷史給他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對于這段時期的議論與反思也比較多,是政治高層、知識群體乃至一般民眾關注的重大話題之一。由于現存五代十國史料大多出自宋人之手,他們對于史料的取舍、編排與評價有著自身的標準,因此也大大影響了后世對五代十國的記憶與研究。正因為此,史學界通常認為,人們對五代十國一無是處、混亂黑暗的認識,是受到宋人“陳腐觀念”[6]的影響。然而,宋人的觀念卻似不可以“陳腐”一言而概之。他們對五代十國史的關注與思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兩宋社會的發展與價值評判的變異,宋人對五代十國的認識也始終體現著活躍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研究群體中,也存在著不同的關注重點與判斷尺度。他們的追念、傷痛、憤懣、鄙夷、期待、幻化,種種復雜而又難以厘清的思想情感,皆在數百年間關于五代十國史的著述與議論中隱隱再現,至今讀起來,仍令人唏噓感嘆。同時,他們關于五代十國的反思、考量、鑒知、比照,諸多理性提升與焦慮,又在兩宋的體制架構、政治實施與意識形態取向等方面留下了深刻烙印。
遺憾的是,如此復雜而活躍的變化并沒有被后人所留意,人們注意到的只是宋人對五代十國的鄙夷與抨擊,以及五代十國不值一提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后世所承襲的,只是北宋中后期乃至南宋時期有關五代十國的歷史記憶,并且做了發揮。以對后晉名臣桑維翰的評價為例。桑維翰是高祖石敬瑭的主要謀士。他力助石敬瑭以割地稱臣、父事契丹的代價,借契丹之力篡奪后唐江山,因此被后世斥為“賣國賊”[7]、“民族敗類”[8]。不過,在北宋,上至宋太祖,下至王禹偁,均對桑維翰十分推崇,就連歐陽修與司馬光對他的態度都極為溫和。即使是在民族意識高漲、理學興盛的南宋,對桑維翰的批判日漸加重,但也仍然存在一定爭議。相對于張浚、朱熹、陳傅良等人的批判,胡寅認為桑維翰雖有謀國誤國之罪,但“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9]。陳亮將其與唐高祖李淵、郭子儀并列,批評他們行“天下之末策”,“借夷狄以平中國”,令后世大受其患,痛斥“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但也仍然將他們視為“明君賢臣”,認為三人“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于此極”[10]。陳誠之、吳曾、劉克莊等人也對桑維翰予以了肯定。直到南宋滅亡以后,桑維翰才被牢牢地釘到歷史的恥辱柱上,成為“萬世之罪人”[11]。非止桑維翰,人們對五代十國諸多現象與人物的認識與評價,都存在著值得關注的變化。
兩宋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存在著不同階段、不同群體、不同指導思想、不同領域之分。就階段而言,可分為宋初三朝、北宋中后期與南宋三個時期;就群體而言,可以分為最高統治階層(以太祖、太宗與趙普為代表)、學者(主要指中原地區學者以及北宋統一多年之后的學者)、十國遺民之分[12];就指導思想而言,北宋中后期的《春秋》學與南宋時期的理學思潮,對于不同時期的五代十國史研究都有著重要影響。從研究領域來看,宋人較為注重對五代十國政治、軍事的研究,而于制度、經濟、文化領域較為漠視。在不同的研究階段、研究群體及理論指導下,宋人筆下的五代十國史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面貌。兩宋對五代十國史的記憶構建與研究,因應了宋人的時代課題,躍動著豐富的變化與特定的時代氣息,為后人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也大大影響了他們對五代十國史的歷史記憶。
二 研究綜述
有鑒于此,兩宋時期關于五代十國史的基本研究脈絡有待被厘清。在這條脈絡中,不同時期的研究特點,不同著述對史料的取舍、評價,不同指導思想所呈現的不同歷史面貌,各國地位的浮沉,等等,都是值得挖掘之處。長期以來,史家大多局限于對《舊五代史》《新五代史》《資治通鑒》這幾部主要著作的研究,而未從宏觀角度對宋人的五代十國史研究進行總體把握,遑論對民間私著,尤其是十國遺民著述的分析與比較。即使是對《舊五代史》《新五代史》《資治通鑒》,也大多聚焦于對其文本的研究,集中于史學史意義上的討論,而于其中所呈現的五代十國的歷史面貌、對五代十國的不同認識與理解等狀況研究不足。本書不揣淺陋,擬從兩宋總體切入,討論宋人如何看待這段晚近的歷史記憶,這些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現實與施政思想起到了何種作用,時代的不同與研究群體的不同又是如何改變了他們看待這段歷史的方式,并澄清學界存在的一些認識誤區,以期以更為寬廣的視野來看待宋人關于五代十國史的研究。
(一)關于《舊五代史》的研究成果
《舊五代史》成書以后,評價不高,相繼有《五代史闕文》《五代史補》等出現,以補其內容之闕。此后,由于《新五代史》的傳世,《舊五代史》逐漸佚失,直至清代修《四庫全書》時,方為邵晉涵于《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等史料中輯出。該輯本曾得到梁啟超的高度評價,但也存在著漏輯文獻、因政治忌諱而篡改原文等問題。關于《舊五代史》,《四庫全書》史臣評論:“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跡,往往以此書為證。雖其文體平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借以獲傳,實足為考古者參稽之助。”[13]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人也從體例、取材等方面對《舊五代史》進行了評述。
對《舊五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清輯本的整理研究方面。1933年,溫廷敬發表《〈舊五代史〉校補序》,但未見著作。陳垣最早對清輯本作了較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他相繼發表《以〈冊府〉校〈薛史〉計劃》《〈舊五代史〉輯本發覆》《〈舊五代史〉輯本引書卷數多誤例》[14]等文,指出清輯本存在著竄改文字、引書卷數有誤等問題,并提出以《冊府元龜》校《舊五代史》的思路,為《舊五代史》的重新整理提供了重要的啟發意義。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舊五代史》整理本。此后,學者們圍繞著清輯本和中華本的文字校勘、點校和考訂做了進一步研究[15],并進行了內容的輯補工作[16]。除了對《舊五代史》零散史料的校補,重新整理輯補《舊五代史》的工作也一直在醞釀中。陳智超相繼撰文,認為現行《舊五代史》是輯本,與原本有較大差距,因此致力于確定《舊五代史》紀傳與諸志的“標準本”,最大限度地還原《舊五代史》的原貌,準備做出一個可以取代輯本的新文本——《輯補舊五代史》。[17]1999年,陳尚君在《學術月刊》第9期發表《清輯〈舊五代史〉評議》,提出了重新整理《舊五代史》的構想。2005年,陳尚君輯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出版,對《舊五代史》清輯本做了很大的增補、刪除、改動和修正工作,同時附錄了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遺文100多萬字。2007年,他發表《〈舊五代史〉重輯的回顧與思考》,記述了編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的過程及反思,認為在《梁太祖紀》的文本處理、對清輯本的增刪調整和諱改文字的回改,以及五代實錄的處理方式等方面,皆可再予斟酌,并從士族社會的解體、五代政治運作中的文武分治和經濟復蘇等方面,發表了對五代社會變化的看法。[18]2016年,由陳尚君主持修訂的《舊五代史》修訂本出版。
此外,陳登原從史學史的角度探討了《舊五代史》湮沒的原因及過程,認為《舊五代史》具有“真價值”,“以撰史之時機言,以取資之材料言,以書中之內容言,《薛史》均有不可掩沒之理”。[19]劉仁亮《薛居正與〈舊五代史〉述論》對《舊五代史》的編纂體例與資料價值作了簡要分析,并就薛居正的史學思想進行了分析,指出癉惡彰善、善惡并書是其史學思想的一大特點。雖然不能擺脫天命論、運數論的束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天命觀的支配作用。[20]單遠慕《薛居正和他的〈舊五代史〉》也對《舊五代史》的作者、體例、內容、觀點作了簡要分析。[21]在近年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中,也出現了對《舊五代史》整體或對其史論的研究。[22]
(二)關于《新五代史》的研究成果
《新五代史》問世后,得到了宋人的高度評價。梅堯臣、劉敞、歐陽發、蘇轍、陳師錫、吳充、王辟之、宋神宗等皆盛贊其春秋筆法,認為法嚴辭約,褒貶得法,遠勝《舊五代史》。也有一部分人對其提出了批評。吳縝撰《五代史纂誤》,從史實的角度對其提出了批評;蘇軾、劉攽因該書未為韓通作傳,而認為只能算是第二等文字;王安石批評其文辭多不合義理。司馬光于《資治通鑒》的五代部分,取事多取《舊五代史》,人物評價則近于《新五代史》。由于順應封建社會后期統治階層和社會學術思潮的要求,《新五代史》逐漸取代《舊五代史》,成為官方史書。清代四庫館臣對二史加以比較,認為《新五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并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為史之優劣矣”[23]。章學誠批評《新五代史》“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24],梁啟超對《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頗有微詞。金毓黻則認為《新五代史》卷帙雖不及薛史之半,但“頗能多所訂補,于五代末季及十國事并四夷附錄,尤能增入新史實”[25]。陳寅恪對《新五代史》所貫注的思想頗為贊賞,“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26]。
對《新五代史》文本的校勘、史實的考訂及各種補、注之作也紛紛出現。錢大昕在《廿二史考異》中注重訂正分析其史料;趙翼一方面對五代的一些社會現象做了研究,另一方面對新、舊《五代史》的取材、體例、失檢處等加以比較與評析,認為“歐史專重書法,薛史專重敘事”[27];王鳴盛認為歐史將梁、唐、晉、漢、周合在一起記事的體例甚為不妥,并對其刻意模仿《春秋》筆法深為不滿,“若非《舊史》復出,幾嘆無征”[28]。他如吳蘭庭《五代史記纂誤補》,吳光耀《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周壽昌《五代史記纂誤補續》,劉光賁《五代史校勘記》,徐炯《五代史補考》,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宋祖駿《補五代史藝文志》,徐炯《五代史記注補》,彭元瑞、劉鳳誥《五代史記補注》等皆對五代史事的補充、糾謬與考訂做出了貢獻。2016年,由陳尚君主持修訂的《新五代史》修訂本出版。
在各種中國通史,及中國史學史著作[29]中,對《新五代史》皆有評介,但介紹相對簡略,褒貶大致同上。在關于歐陽修的傳記與研究著作[30]中,作為歐陽修學術成就的一部分,《新五代史》也被加以評介,但大多沿襲前人之說。學者們還對歐陽修在《新唐書》《新五代史》和《集古錄》等著作方面的史學成就做了研究,大多持肯定態度,但也有學者對其提出了批評。[31]
對《新五代史》的專門研究比較活躍。主要有:
石田肇對《新五代史》的編纂內容及其方法進行了總結和歸納。[32]林瑞翰從書法、記事、考史和史源四個方面對《新五代史》進行了考察,認為《新五代史》書法謹實、無諱并寓褒貶;在記事上有詳于《舊五代史》者,但由于《新五代史》文省,刪略的材料也不少,因此不可忽略《舊五代史》的史料價值;《新五代史》對《舊五代史》內容也有諸多考訂;《新五代史》史源廣博,很多文字采自《舊五代史》以外的文獻。[33]宋馥香、王海燕總結了《新五代史》的編纂特點:以“不沒其實”的原則確定史書編纂義例,以《春秋》褒貶書法和類傳形式風勵臣節,以拾遺、糾謬和“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的原則改造舊史“志”。[34]
杜文玉、羅勇總結了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體現出的史學思想,即“不沒其實”、秉筆直書的思想,反對“天人合一”讖緯迷信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主張“攘夷”及大一統說思想,以“忠孝”為標準評價歷史人物的主導思想,以史為鑒、重視經世致用的思想。[35]王天順認為,《新五代史》是在當時的政治空氣和學術空氣影響下,把《春秋》之學和史學相結合的一次成功嘗試。從義例和書法來看,歐史采取“不沒其實”、“別嫌明微”、“責以備,推以恕”的褒貶原則,三者都不離“正名以定分”,“求情以責實”的宗旨;從褒貶內容來看,歐史強調臣節,強調忠孝統一,不忘攘夷。[36]姚瀛艇認為正名分是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的出發點和歸宿。《新五代史》人物評價所依據的標準是:君臣之義是無論皇帝如何,都必須為之盡忠;以“不妄以予人”的原則來表彰忠臣義士,對亂臣賊子,則區分情況予以分別對待,如弒君為臣子之大惡、區別“反”與“叛”的性質、區別主動謀反與被迫而反、以“伏誅”來表示謀反、叛變的頭子的死;對五代亂君,以正其篡弒之罪、著其禮樂之壞、譏其刑政之失、刺其骨肉之變等形式,列舉其“亂”,使他們起到“反面教員”的作用。[37]
柴德賡指出,《新五代史》對后人認識五代歷史起到了極大影響,其獨享盛名的原因,一方面是文章好,另一方面是其比《舊五代史》更能為封建統治服務,更符合封建政權的需要。[38]吳懷祺認為,歐陽修在史學領域內發展了北宋的春秋學,并在一些重要方面突破了北宋春秋學的觀點。同時,歐陽修的理學思想雖然沒有成為體系,但是理學對史學的影響已經在他的史學中反映出來。[39]蔡崇榜認為義理派史學始自《新五代史》[40],錢茂偉認為《新五代史》表現出來的是“理學化史學”[41],羅炳良在論及宋代義理化史學時,也是從《新五代史》入手討論[42]。盛險峰認為,《新五代史》除受《周易》和《春秋》影響外,還體現了宋學的特征,但與理學尚存一定距離。《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統的雙重關照,它使歐陽修成為唐宋時期道和道統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43]吳業國認為忠節禮義是北宋禮制建設的核心,作為禮制建設的踐行者,歐陽修著成《新五代史》,以“春秋精神”表明褒貶,是宋代禮制建設的重要成果。[44]
倉修良、陳仰光、陳光崇等對尹洙在《新五代史》撰修過程中的角色進行了討論。[45]張金銑、楊光華、李勃等對新五代史的內容進行了考訂。[46]顧宏義認為:《新五代史》未為韓通立傳,主要與宋代官史對韓通的定性,以及與北宋中期黨爭趨于激化有關,對學界普遍認為的“為本朝諱”說提出了質疑。[47]
對《新五代史》宏觀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楊昶、姚偉鈞就《新五代史》的撰寫時間、《新五代史》與《舊五代史》的優劣、《新五代史》記事似司馬遷的問題、《新五代史》的春秋筆法等問題作了探討。[48]曹家齊則從歷史背景出發,探討了《新五代史》的產生、特點以及重大影響。他認為,《新五代史》的目的是以史學正人心,是在儒家倫理綱常受到內憂外患與佛、道二教的沖擊之下確立的。因此,“歐陽修修撰私史遂具有了一種與當日儒學復興聲氣相通的意義,或者說是北宋儒家復興在史學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49]。張明華對《新五代史》的體例和內容進行了研究,對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體現的歐陽修的政治、哲學思想進行了評述與分析,并對徐無黨的五代史注文與吳縝的《五代史纂誤》進行了研究。[50]
關于《新五代史》注文的研究,有班書閣《五代史記注引書考》《五代史記注引書檢目》等。[51]張承宗總結評述了徐無黨注文的特點[52],吳懷祺和康建強、余敏輝等認為徐無黨的《新五代史》注文未能表達歐陽修的著史宗旨,甚至有悖于歐陽修史學的基本精神,張明華則持相反觀點。[53]
關于新、舊《五代史》比較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陶懋炳強調著眼于史家或史書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時代思潮去考察二史,比較二史體例、史料舍取及史學思想,認為二史各有優劣。[54]何宛英從史料舍取、編纂體例、行文風格等方面比較了兩史的異同,并考察了異同之根源,認為私家獨撰與官修眾著這兩種不同的修史程序和不同歷史時期史家所面臨的政治任務是其相異的主要原因,而相同之處皆反映了史學為政治服務這一傳統史學的根本宗旨。[55]趙維平認為薛史熱衷于論說君臣之道,強調天命,歐史則對朋黨利弊和宦官伶官之害予以充分及深刻的評述,重人事。歐史史論基本以儒家學說為根據,薛史則寬泛許多。[56]姜海軍認為二史分處于兩個時代,是漢學與宋學兩種經學范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體系的具體體現。[57]
總體而言,對《舊五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文本的考訂、輯補、校勘工作,而關于這一時期宋人如何看待五代十國的歷史則較少涉及。學界對《舊五代史》的史料價值較為認同,但對其諱飾之處頗有微詞。不過,對其諱飾之處,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舊五代史》撰成時,尚有北漢等諸國未入宋朝版圖。因此,對于十國,《舊五代史》的態度如何,對史料如何取舍與評價,都是史學界未曾深究的問題。[58]宋初關于五代十國的著述甚多,與后世較為統一的思想相比,這一時期思想駁雜,尤其以十國遺民的著述為多。他們與《舊五代史》有哪些不同的看法,關注的焦點又在哪里,都是值得注意的。對《新五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編纂體例與內容、史學思想、糾謬補闕等方面,學者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于對其文本特點的研究,五代十國的歷史只是為了作為例證附屬出現。而歐陽修對于五代的認識、對于十國的態度,都是值得進一步深究的課題。
(三)關于《資治通鑒》五代部分的研究成果
《資治通鑒》甫一問世,就得到宋人的高度重視。此后,很多學者對其進行研究,并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通鑒學”。宋末元初,胡三省為《資治通鑒》作《資治通鑒音注》,王應麟作《通鑒地理通釋》。明代嚴衍、談允厚撰《資治通鑒補》,對《資治通鑒》和《資治通鑒音注》的謬誤進行了考訂。清人張敦仁選擇《資治通鑒補》中的改正、存疑、備考、補注等部分,編成《通鑒正略》。清人陳景云《通鑒音注舉正》、錢大昕《通鑒注辨正》,都是研究《資治通鑒》的重要參考書。
近代以來,出現了一些帶有總結和開拓性的著作。其中崔萬秋的《通鑒研究》是最早研究《資治通鑒》的總結性著作。[59]張須(即張煦侯)的《通鑒學》幾乎把前人研究《資治通鑒》的成果搜羅殆盡,同時又自成體系,是研究《資治通鑒》的重要學術著作。[60]陳垣的《通鑒胡注表微》,則對胡三省的生平、抱負、學術思想、治學精神等各方面做了詳盡的全面研究。[61]在中國通史及中國史學史著作,以及司馬光的傳記[62]中,對《資治通鑒》皆有評介。關于《資治通鑒》的研究論文及著作甚夥,《〈資治通鑒〉叢論》和《司馬光與〈資治通鑒〉》是兩本重要的論文集。[63]學者們對《資治通鑒》的編纂體例、長編分工、史源、史學思想[64]等相關問題都做了大量研究,成果頗豐。
但是,關于《資治通鑒》五代部分的專論很少,主要集中于對五代長編分修問題的討論[65],而于司馬光對五代十國的認識和研究涉及不多。
(四)關于其他著述的研究成果
在總述宋代史家關于五代十國的史學著述方面,王德毅選擇《舊五代史》等主要的十三部著作進行了簡要評介,并指出南唐與北漢在宋代后期地位有所提高。[66]郭武雄著重對五代實錄進行了分析,認為其在宋朝史書中有著大量存留。[67]劉兆祐、林平、張興武、Johannes L.Kurz均有關于宋人對五代十國著述的介紹。[68]但這些介紹在某些著述是否為宋人所作方面存有爭議,有進一步厘清的必要。
相比《資治通鑒》與《新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研究成果較少。除了在李燾的研究論文及著作中有所涉及[69],主要集中于其文本的點校、勘誤、考訂、輯佚,以及編纂體例及特點(尤其是長編法)[70]、史料來源與取材[71]、版本沿革及史料價值[72]、史學思想[73]等方面。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就該書的版本、撰修始末、取材、注文及史料價值等問題作了系統論述。[74]
但這些研究基本上沒有觸及五代十國的存在。《續資治通鑒長編》所敘述的是建隆元年(960)之后的北宋史事,主要保存的是尚未入宋的南唐、北漢、吳越等國的史料,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只占很小的份額,但所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南宋時期關于五代十國史研究特點的變化,值得加以挖掘與探討。
在宋人關于十國的著述中,以南唐、吳越、后蜀為多。但今人對這些著述的研究甚少。如《五代史闕文》未見專文論及,拙文《先天不足的“千古信書”——〈江南錄〉》對《江南錄》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75]關于《蜀梼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對其點校成果,以及對其版本源流及史料價值的考述。[76]對《吳越備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作者、成書過程、版本源流的考證,以及文獻的補正。[77]關于《九國志》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對該書作者、史料價值、版本流傳及治史特點的考釋。[78]對《北夢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該書的作者、結集時間、文獻來源、史料價值、校勘輯佚,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對《北夢瑣言》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79]《十國紀年》的存佚時間、《釣磯立談》的作者、《江南野史》的作者考訂與史料價值、《五代春秋》對《春秋》書法的繼承等問題也為學者所論及。[80]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對文本自身特點的挖掘,而于其所反映的五代十國歷史面貌未加探究,也少見對同一史事或人物的專門分析比較研究。尤其是十國遺民的著述與北宋官方文本之間存在諸多不同,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較少,大多零散地分布于專論其他問題的論文或著作中,作為證明某一觀點的細微例證而存在。張邦煒《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問題的史源學思考》就后蜀后主孟昶“七寶溺器”可信與否以及孟昶所著官箴是否存在進行討論,并就孟昶在北宋官方與蜀地士人所作文本中的不同形象進行了探討。[81]
在今人關于十國的著述中,以對《南唐書》的研究最多。關于《新修南唐書》的作者問題,盧葦菁認為不是陸游,陳光崇、朱仲玉、劉永翔、雷近芳則持相反觀點。[82]關于該書的史學思想及治史特色,陳光崇認為,陸游《南唐書》簡核有法,增補了史料;表彰“盡忠所事”的愛國精神,抨擊置國家危亡于不顧之人;排斥宗教迷信;重視南唐興亡的經驗教訓;缺點是對南唐的文物制度沒有予以足夠重視,一些人物如大臣湯悅、名僧應之等缺而不載,一些史實也互相抵牾。[83]朱仲玉認為,陸游作該書的目的是希望南宋統治階級以史為鑒;在歷史編纂學上既重視史學傳統又有獨創;既重視文字材料,也重視調查訪問等口頭資料。[84]雷近芳認為,該書貫穿愛國主義思想;注意總結統治經驗和教訓;客觀評價歷史人物;歷史觀較為進步;文筆簡賅,選材編纂皆有法度,并且增補保存了一些南唐史料。[85]鄭滋斌對陸游《南唐書》的本紀部分進行了逐年考訂,并將其他存世文獻的相關材料羅列于后,詳加比對。[86]就三家《南唐書》的流傳及版本,學者也進行了研究。[87]關于胡恢《南唐書》,陳光崇考證了胡恢的生平,并引用宋人蘇頌對該書的意見,對其相關問題進行了考釋。[88]關于馬令《南唐書》,張剛、孫萬潔認為其取材廣泛、體例有所創新、史事及人物評論較為客觀公允,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89]在近年的碩士學位論文中,也有關于南唐史著的研究[90],討論重點大多集中于特定著作的作者、體例、文獻價值等方面。
三 研究空間
到目前為止,就兩宋關于五代十國史的研究狀況而言,尚缺乏全面與系統的梳理。以往關于宋人五代史觀的研究,所依據的主要文獻為新、舊《五代史》,對大量的其他相關文獻如《江南錄》《五代史闕文》《長編》等有關五代十國的史料關注不足,對在兩宋的不同階段、不同群體、不同指導思想之下所呈現的五代史觀的差異關注亦有不足。有鑒于此,本書擬在全面梳理大量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宏觀的角度對宋人的五代十國史研究進行總體把握,通過系統的研究揭示其發展演化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指導思想之展開與互動,從動態的角度探討“五代”與“十國”地位在兩宋的變化。在研究中,不止于作學術史的探討,更求揭示這一領域所包含的文化意義。
四 研究框架
本書是對兩宋關于五代十國史研究狀況與記憶構建的系統梳理和整體研究。主要框架如下:
第一章搜錄了兩宋專述或主要記述五代十國歷史的著述,時間斷限以五代十國諸政權各自入宋的實際時間為準,諸政權入宋之前所產生的著述不錄在內。同時,簡要探討了它們所呈現出的特點。
兩宋專述或主要敘述五代十國史事的著述有七十余種。其中以敘述十國史事者為多,但以主要論述五代中原王朝的著述影響為大。以北宋的著述為多,南宋時期則較少,而北宋時期的著述又呈現出兩個不同的階段。十國著述中以南唐最多,多為南唐遺臣、遺民之作;其次是吳越,作者多系吳越王室子孫;再次是關于前后蜀的著述。
第二章探討了宋初三朝關于五代十國的研究,分別討論了這一時期的研究特點、宋人對五代十國歷史地位的認識、政治高層及史學領域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其中,以宋初德運之爭為重點,討論了五代的總體歷史地位,以及后梁的矛盾地位;以太祖、太宗、趙普為代表,討論了北宋政治高層對五代十國經驗教訓的汲取;以《舊五代史》為中心,討論了宋初三朝官方對五代史的研究;以《五代史闕文》為重點,討論了民間對五代史的研究;以《舊五代史》的十國部分、《江南錄》為代表,討論了官方對十國史的研究;以南唐、吳越、后蜀的民間著述尤其是十國遺民的作品為重點,討論了它們的著述特點,以及與官方文本的不同。
在不同的研究群體中,存在著不同的關注重點與價值判斷。其中最高統治階層的深度參與及認真反思,及其立國方針的極具針對性,都是歷朝罕見的,也是五代史研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作為官修正史,《舊五代史》透露出諸多值得關注的信息,其諱飾與直筆、所持忠節標準、對天命與人事的態度、關于君臣之際的討論等,均存在挖掘與探討的空間。而且,它所描繪的五代十國史與后世的印象較為不同。由于《舊五代史》的主要目的是為宋廷提供治國的經驗教訓,因此政治架構、經濟狀況、軍事體制、思想文化等均一脈相承的中原五朝便成為關注重點,加之當時尚未統一,遂造就了《舊五代史》對十國史的漠視與貶低,呈現出濃厚的正統意識,并突出顯示了北宋的皇恩與天威。與對中原五朝相對寬容的評價標準不同,《舊五代史》對十國政權與人物的評價呈現出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特點,這與民間私著尤其是遺民筆下的十國史有明顯不同。兩種文本的相互對照,使五代十國的歷史呈現出耐人尋味的不同面貌。在十國中,南唐史受到北宋政府的重視,并專門編修了官方南唐史《江南錄》。這部史書雖然已經佚失,但在殘留的片斷與時人的評價里,仍然透露出不少有價值的信息。《五代史闕文》則以倡忠義、重氣節的著述主旨,開后世《新五代史》等以尊王忠君為主旨的五代十國史研究的先河。
這一時期有關五代十國史的撰著相當活躍,而有關五代十國史的思考則較為蒼白和淺散,但同時也顯現出樸素平實的面貌,有助于后人從中得出更為客觀的認識。不同于后世對五代十國史的印象,這一時期的著述尚存在著對五代十國的一些正面描述。同時,由于不同階層與群體的介入,有關五代十國的研究與后世較為統一的指導思想與論述相比,呈現出另一番多元化而活潑的生氣。
第三章探討了北宋中后期關于五代十國史的研究狀況及特點。分別就這一時期宋人對五代十國史歷史地位的認識與研究特點、《新五代史》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資治通鑒》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及特點進行了探討。
這一時期是兩宋五代十國史研究的重要轉折點。隨著“防弊之政”的完成,文人社會的穩固確立,武夫當道的五代受到了宋人的普遍鄙夷,五代十國的正統地位遭到強烈質疑。他們注重五代亂象與社會現實的緊密結合,防止五代亂象的重演尤其成為文人集團念茲在茲的集體意識,也有部分人開始關注由五代矯枉過正的一些弊端。新的學術思潮的涌現,又使學者以新的指導思想與研究手法重修五代十國史的熱情高漲。例如,在北宋《春秋》學的巨大影響下,將五代綱常紊亂、禮崩樂壞的歷史教訓提到極為突出的層面,認為這是五代衰亂的重要原因。這與宋初更加注重現實政治制度的措置明顯不同。除了關于五代正統地位的爭論、對五代歷史地位的普遍貶損外,宋人的五代史著述也呈現出從取材到評論“矮化”五代的趨向,甚至出現了否定五代正統地位的著作《唐余錄》。以歐陽修的《新五代史》為代表,開啟了對五代十國史的全面否定時期。這一時期關于五代十國的代表性著作是《新五代史》與《資治通鑒》的五代部分,二者各從不同角度對五代十國的歷史進行了反思,后人對五代十國的認識基本上來源于此。
第四章探討了南宋的五代十國史研究。分別討論了宋人對五代十國歷史地位的認識、《續資治通鑒長編》對五代十國史的研究,以及陸游《南唐書》對南唐史的研究。
不同于北宋以中原王朝為正統所在,南宋開始為偏居一方的政權爭取正統,位于中原地區的五代地位隨之徹底淪落,而十國中南唐、北漢的地位則相對上升。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的五代十國部分和陸游的《南唐書》為代表。前者的主要特點是忽視與貶低五代十國,人物刻畫趨向負面與臉譜化,并突出宋朝的英明神武與仁義道德。后者則進一步提升了南唐的地位,并對南唐的歷史作了深刻反思,反映了時局變化對史家的影響。
第五章是個案研究。主要討論了五代頻繁發生的擁立帝王現象,及兩宋對馮道的評價及特點。
五代兵驕將悍,擁立新主者眾。五代諸君中,李嗣源、郭威皆是黃袍加身,由無預謀地被擁立到有意識地利用,一次比一次精巧。北宋的建立亦襲其故智,經過周密計劃之后,奪取了后周的江山。此類題材對宋人而言,既有敏感性,又有一定的誘惑性,因而圍繞著五代發生的若干“擁立新君”事件,形成了值得專題研究的個案。
馮道是五代文官的標志性人物。他從五代備享尊崇,到后世飽受詬詈,其間轉折正發生在宋代,反映了深刻的思想變遷,并大大影響了后世對馮道的評價。因此,梳理宋人對馮道的研究脈絡,澄清學界存在的某些理解誤區,并歸納出宋人研究馮道的若干特點,可以通過更廣闊的視野來認識“馮道現象”,具體而深刻地把握宋人的五代十國觀。
注釋
[1]陶懋炳:《五代史略·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頁。
[2]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前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頁。
[3]鄭學檬:《五代十國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頁。
[4]陶懋炳:《五代史略·序》引熊德基語,第7頁。
[5]錢穆:《國史大綱》下冊,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502頁。
[6]陶懋炳:《五代史略·序》第7頁。
[7]陶懋炳:《五代史略》,第234頁。
[8]卞孝萱、鄭學檬:《五代史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
[9](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胡明仲本末》,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03—104頁。
[10](宋)陳亮:《陳亮集》卷八《酌古論·桑維翰》,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91—93頁。
[11](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九《五代中》,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63頁。
[12]最高統治階層主要以太祖、太宗與趙普為代表,在北宋前三朝表現得極為活躍。雖然兩宋很多學者也是官員,位居統治階層,但太祖、太宗、趙普等人掌握著國策的制定權,占據著政策措置的最高點,其針對五代十國史的反思與舉措較他人具有更為鮮明的特點。十國遺民雖然也可以歸入學者之列,但因其作品與中原地區學者以及統一多年之后的學者作品相比,思想感情與關注重點均有所不同,因此特將十國遺民另列。
[13](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舊五代史”條,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411頁。
[14]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
[15]如梁太濟《薛史“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為什么“一般不再改回”——對〈舊五代史〉點校本的一點意見》,《內蒙古大學學報》1977年第5期;程弘《讀〈舊五代史〉札記》,《文史》第16輯,1982年;周征松《〈通歷〉續篇和〈舊五代史〉的校補》,《山西師大學報》1982年第1期;樊一《點校本〈舊五代史〉“王衍傳”斷句質疑一則》,《文史》第19輯,1983年;董恩林《〈舊五代史·食貨志〉校考》,《華中師范學院研究生學報》1984年第1期;蘇乾英《〈舊五代史·黨項傳〉族性蕃名考》,《復旦學報》1985年第1期;湯開建《〈《舊五代史·黨項傳》族性考〉質疑》,《寧夏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張其凡《校點本〈舊五代史〉獻疑(九則)》,《安徽史學》1985年第3期;張其凡《三史(〈通鑒〉、〈舊五代史〉、〈宋史〉)點校本獻疑——讀史札記(三十六則)》,《古籍整理與研究》1987年第1期;朱玉龍《中華版〈舊五代史〉考證》,《安徽史學》1989年第2、4期,1990年第2、3期;齊勇鋒《標點本新、舊〈五代史〉校勘拾零》(一),《標點本新、舊〈五代史〉校勘拾零》(二),《文史》第33輯,1990年;于學義《〈舊五代史〉、〈資治通鑒〉證誤各一則》,《史學月刊》1991年第2期;余和祥《〈舊五代史·外國列傳〉考實》,《中南民族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宋玉昆《〈冊州元龜·舊五代史〉補校掇瑣》,《新世紀圖書館》1992年第5期;潘學忠《〈舊五代史〉質疑一則》,《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4期;陳尚君《〈永樂大典〉殘卷校〈舊五代史〉札記》,《書品》1994年第1期;鄭杰文《〈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點校獻疑》,《歷史教學》1994年第3期;宋玉昆《〈冊府元龜〉中的〈舊五代史〉補校議》,《江蘇圖書館學報》1995年第5期;陳尚君《貞石訂五代史》,《海上論叢》第3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徐時儀《讀〈舊五代史〉札記一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第1期;董恩林《〈舊五代史〉校讀札記》,《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1年第6期;董恩林《〈舊五代史〉考證》,《文史》2002年第1輯;李全德《點校本〈舊五代史〉校誤》,《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1期;張明華《新舊〈五代史〉地名勘誤一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1期;周阿根《〈舊五代史·薛貽矩傳〉校補》,《江海學刊》2013年第1期;孫先文《〈舊五代史·唐書〉勘誤一則》,《蘭臺世界》2016年第7期;鄭慶寰《輯本〈舊五代史·地理志〉所收“十道”內容辨析》,《唐史論叢》2016年第2期;等等。
[16]如胡文楷《〈薛史·王仁裕傳〉輯補》,《中華文史論叢》1980年;張凡《〈舊五代史〉輯補——輯自〈永樂大典〉》,《歷史研究》1983年第4期;陳尚君《〈舊五代史·王審知傳〉輯校》,《漳州師院學報》1995年第1期;陳尚君《〈舊五代史〉補傳十六篇》,《文獻》1995年第3期;等等。
[17]參見陳智超《〈舊五代史〉輯本之檢討與重新整理之構想》,《史學史研究》1999年第4期;《論重新整理〈舊五代史〉輯本的必要與可能——〈舊五代史〉輯本及其點校本》,《陳智超自選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陳智超《輯補〈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導言》,《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一輯,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陳智超《輯補〈舊五代史〉列傳導言》(上、中、下),分見《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二輯、第三輯、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013年、2014年版;陳智超、鄭慶寰《〈舊五代史〉諸志標準本的論證》,《江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陳智超、張龍《輯補〈舊五代史·梁太祖本紀〉導言(續)》,《史學集刊》2013年第5期;等等。
[18]陳尚君:《〈舊五代史〉重輯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2007年第2期。
[19]陳登原:《薛氏〈舊五代史〉之冥求》,《東方雜志》1930年第27卷第14期,見《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
[20]劉仁亮:《薛居正與〈舊五代史〉述論》,《河北師院學報》1991年第2期。
[21]單遠慕:《薛居正和他的〈舊五代史〉》,《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22]孫先文:《〈舊五代史〉研究》,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于小曼:《〈舊五代史〉史論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23]《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新五代史”條,第411頁。
[24](清)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三〇《信摭》,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頁。
[25]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86頁。
[26]陳寅恪:《寒柳堂集·贈蔣秉南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82頁。
[27](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51頁。
[28](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三《歐法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4頁。
[29]如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倉修良《中國古代史簡編》,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劉節《中國史學史稿》,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等。
[30]如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4年版;蔡世明《歐陽修的生平與學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劉若愚《歐陽修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洪本健《醉翁的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黃進德、郭璇珠《歐陽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劉德清《歐陽修論稿》,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劉德清《歐陽修傳》,哈爾濱出版社1995年版;黃進德《歐陽修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盧家明《歐陽修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劉德清《歐陽修》,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顧永新《歐陽修學術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31]如趙呂甫《歐陽修史學初探》,見吳澤《中國史學史論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姚瀛艇《歐陽修的史論》,《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陶懋炳《評歐陽修的史學》,《湖南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陳光崇《歐陽修的史學成就》,《社會科學輯刊》1982年第1期;陳光崇《歐陽修的史學》,見鄧廣銘、程應繆《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宋衍申《歐陽修治史的求實精神》,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二),岳麓書社1983年版;王繼麟《歐陽修思想及史學評價淺議》,見《宋史研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劉德清《歐陽修史學觀簡論》,《信陽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2期;吳懷祺《易學理學和歐陽修的史學》,《安徽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顧永新《歐陽修編纂史書之義例及其史料學意義》,《文史哲》2003年第5期;等等。
[32]石田肇:《〈新五代史〉的體例》,《東方學》1977年第7期。
[33]林瑞翰:《歐陽修〈五代史記〉之研究》,宋史座談會《宋史研究集》第十輯,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8年。
[34]宋馥香、王海燕:《論歐陽修〈新五代史〉的編纂特點》,《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
[35]杜文玉、羅勇:《〈新五代史〉與歐陽修的史學思想》,《贛南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
[36]王天順:《歐陽修的〈五代史記〉和他的“春秋學”》,《南開史學》1984年第1期。
[37]姚瀛艇:《論〈新五代史〉的人物評價》,見《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1輯。
[38]柴德賡:《論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見柴德賡《史學叢考》,中華書局1982年版。
[39]吳懷祺:《對歐陽修史學的再認識》,《史學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0]蔡崇榜:《〈唐鑒〉與宋代義理史學》,《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3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錢茂偉:《范型嬗變的宋代史學》,見張其凡等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頁。
[42]羅炳良:《從宋代義理化史學到清代實證性史學的轉變》,《史學月刊》2003年第2期。
[43]盛險峰:《〈新五代史〉的理性與價值》,《北方論叢》2011年第6期;《道與道統:〈新五代史〉的雙重關照:〈新五代史〉史論與歐陽修的“三論”》,《北方論叢》2013年第2期。
[44]吳業國:《歐陽修〈新五代史〉與北宋忠節禮義的重建》,《河南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
[45]倉修良、陳仰光:《〈新五代史〉編修獻疑》,《山西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陳光崇:《尹洙與〈新五代史〉小議》,《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46]張金銑:《〈新五代史〉勘誤一則》,《中國史研究》1993年第4期;李勃:《〈新五代史·職方考〉補正一則》,《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第2期;楊光華:《〈新五代史〉、〈十國春秋〉正誤各一則》,《文獻》1995年第4期;劉橋:《〈新五代史〉勘誤一則》,《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等等。
[47]顧宏義:《〈新五代史〉未為韓通立傳原因試探》,《史學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8]楊昶、姚偉鈞:《歐陽修〈新五代史〉有關問題探討》,《湖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
[49]曹家齊:《歐陽修私撰〈新五代史〉新論》,《漳州師范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50]張明華:《新五代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51]班書閣:《五代史記注引書考》,《燕大月刊》1930年第10期;《五代史記注引書檢目》,《女師學院期刊》1934年第7期。
[52]張承宗:《〈新五代史〉徐無黨注述評》,《文獻》2001年第3期。
[53]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宋遼金卷》第一章《歐陽修的史學思想》,黃山書社2002年版;康建強、余敏輝:《徐無黨生平學術考略》,《淮北煤炭師院學報》2002年第4期;張明華:《徐無黨辯誣與〈新五代史〉的重新定位研究初探》,《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54]陶懋炳:《新舊〈五代史〉評議》,《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2期。
[55]何宛英:《“兩五代史”比較研究》,《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第3期。
[56]趙維平:《薛居正、歐陽修論史之比較》,《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
[57]姜海軍:《新舊〈五代史〉編纂異同之比較》,《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3期。
[58]拙文《〈舊五代史〉史臣對十國史的研究》(《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就《舊五代史》史臣對十國史的研究作了探討。
[59]崔萬秋:《通鑒研究》,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60]張煦侯(即張須):《通鑒學》(修訂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1]陳垣:《通鑒胡注表微》,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62]如宋衍申《司馬光傳》,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李昌憲《司馬光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63]劉乃和、宋衍申主編:《〈資治通鑒〉論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劉乃和、宋衍申主編:《司馬光與〈資治通鑒〉》,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64]宋衍申:《試論司馬光的史學思想》,見劉乃和、宋衍申主編《司馬光與〈資治通鑒〉》;施丁:《兩司馬史學異同管窺》,見劉乃和、宋衍申主編《〈資治通鑒〉論叢》;孫方明:《論司馬光的史學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于瑞桓:《司馬光的史學思想及其理學精神》,《山東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等等。
[65]倉修良:《〈通鑒〉編修分工及優良編纂方法》,見劉乃和、宋衍申主編《〈資治通鑒〉論叢》;彭久松:《〈資治通鑒〉五代長編分修人考》,《四川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王曾瑜:《關于劉恕參加〈通鑒〉編修的補充說明》,《文史哲》1980年第5期;等等。
[66]王德毅:《宋代史家的五代史學》,見《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
[67]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68]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年;林平:《宋代史學編年》,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張興武:《五代藝文考》,巴蜀書社2003年版;Johannes L.Kurz,“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in Song Times”,見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3(2003)。
[69]如王德毅《李燾父子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王德毅《李燾評傳》,《宋史研究集》第三輯,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6年;張鎰《李燾及其史學》,《史苑》1970年14期;徐規《李燾年表》《李燾年表補正》及《李燾年表再補正》,分別見《文史》第2、4、16輯;徐規《李燾》,《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方壯猷《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王承略、楊錦先《李燾著述考辨》,《文史》50輯,中華書局2000年版;楊家駱《續通鑒長編輯略》,世界書局2009年版;周藤吉之《南宋李燾與〈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成立》,見氏著《宋代史研究》,日本東洋文庫昭和四十四年。
[70]劉復生:《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的編纂》,《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裴汝誠等:《〈續資治通鑒長編〉撰修始末考略》,《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張孟倫:《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3年第4期;裴汝誠:《司馬光長編法與李燾〈長編〉》,《東北師大學報》1984年第5期;裴汝誠:《〈續資治通鑒長編〉義例考略》,《文史》25輯,中華書局1985年版;曹之:《〈續資治通鑒長編〉編纂考》,《圖書館員》1995年第5期;陳其泰、屈寧:《論李燾的歷史編纂學成就——以〈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中心》,《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
[71]如燕永成《今七朝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5期;《〈續資治通鑒長編·神宗朝〉取材考》,《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2]顧吉辰、俞如云:《〈續資治通鑒長編〉版本沿革及其史料價值》,《西北師大學報》1983年第3期。
[73]如蔡崇榜《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史學研究淺見(李燾、李心傳傳)》,《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2期;裴汝誠《李燾的史學成就與治史精神》,《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1年第6期;周征松《一部詳實的北宋史》,《光明日報》2002年1月15日;等等。
[74]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中華書局1985年版。
[75]陳曉瑩:《先天不足的“千古信書”——〈江南錄〉》,《史學集刊》2014年第2期。
[76]如(宋)張唐英著,王文才、王炎校箋《蜀梼杌校箋》,巴蜀書社1999年版;樊一、方法林《張唐英與〈蜀梼杌〉》,《成都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樊一《〈蜀梼杌〉的史料價值與版本源流》,《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等等。
[77]如徐映璞《〈新五代史·吳越世家〉補正》,見《兩浙史事叢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鄒勁風《錢儼和〈吳越備史〉》,《史學月刊》2004年11期;李最欣《錢儼和〈吳越備史〉一文補正》,《史學月刊》2006年第11期;李最欣《錢氏吳越國文獻和文學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何勇強《錢氏吳越國史論稿》,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
[78]李紹平:《路振與〈九國志〉》,《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3期;彭小平:《路振史學著作述略》,《湘潭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岳毅平:《〈九國志〉叢考》,《文獻》1999年第2期;羅威:《〈九國志〉的版本及學術價值》,《長沙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張靜:《〈九國志〉史學研究》,《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年第3期。
[79]如林艾園《〈北夢瑣言〉的史料價值》,《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2年第5期;胡可先《〈北夢瑣言〉志疑》,《徐州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拜根興《〈北夢瑣言〉結集時間辨析》,《文獻》1993年第3期;莊學君《〈北夢瑣言〉研究》,《西南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房銳《對〈北夢瑣言〉結集時間的再認識》,《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7期;等等。房銳:《孫光憲與〈北夢瑣言〉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版。
[80]張友臣:《〈十國紀年〉存亡略考》,《齊魯學刊》1987年第5期;陳尚君:《〈釣磯立談〉作者考》,《文史》第44輯,1998年;燕永成:《龍袞和他的江南野史》,《贛南師范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劉曉明:《龍君章考》,《廣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7期;劉曉明:《龍袞與江南野史》,《文史》2002年第2輯;鄧銳:《尹洙〈五代春秋〉對〈春秋〉書法的繼承》,《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
[81]張邦煒:《昏君乎?明君乎?——孟昶形象問題的史源學思考》,《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82]宏海:《〈新修南唐書〉作者不是陸游》,《文匯報》1982年7月26日;盧葦菁:《〈新修南唐書〉作者考辨》,《史學月刊》1982年第4期;朱仲玉:《陸游的史學成就》,《浙江學刊》1983年第4期;陳光崇:《論陸游〈南唐書〉——兼評〈新修南唐書〉作者考辨》,《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2期;劉永翔:《〈新修南唐書〉陸游著祛疑》,《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6期;雷近芳:《陸放翁治史考》,《信陽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1期。
[83]陳光崇:《論陸游〈南唐書〉——兼評〈新修南唐書〉作者考辨》,《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2期。
[84]朱仲玉:《陸游的史學成就》,《浙江學刊》1983年第4期。
[85]雷近芳:《論陸游的史識與史才》,《史學月刊》1992年第4期。他如柳詒徵《陸放翁之修史》(《國史館館刊》1948年1卷2號,見《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肅霜《陸游〈南唐書〉簡論》(《長沙水電師院學報》1991年第1期);雷近芳《論陸游的史鑒思想》(《信陽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1期);雷近芳、郭建淮《今存南唐史著論略》,(《佛山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馬冰麗《陸游〈南唐書〉簡論》,(見《陸游論集》,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孫淑彥《陸游和〈南唐書〉》(《汕頭日報》1985年1月11日)等也對該書的史學思想及治史特色進行了討論。
[86]鄭滋斌:《陸游〈南唐書本紀〉考釋及史事補遺》,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
[87]楊恒平:《三家〈南唐書〉傳本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第6期;郭立暄:《汲古閣刻〈南唐書〉版本考》,《圖書館雜志》2003年第4期。
[88]陳光崇:《第一部〈南唐書〉的作者胡恢其人》,《史學史研究》1986年第3期。
[89]張剛、孫萬潔:《馬令〈南唐書〉述評》,《今日南國》(理論創新版)2009年第4期。
[90]肖剛:《江南野史研究》,廣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姚萍:《陳彭年及其〈江南別錄〉》,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張剛:《宋人南唐史研究》,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畢琳琳:《鄭文寶及所著南唐二史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王慧:《陸游〈南唐書〉文學價值研究》,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