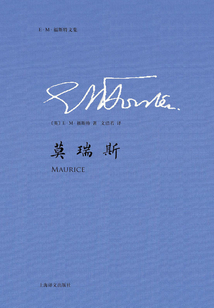
莫瑞斯(同名電影原著)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言
出版于1910年的《霍華德莊園》獲得了成功,卻起到了擾亂福斯特生活的效果。它使他充滿了迷信的預感,生怕自己會失去作家的創作力。隨后他整整焦慮了一年,對本國的生活感到煩惱,無法靜下心來做任何事情。他著手撰寫一部新小說《北極之夏》,然而卻搞得雜亂無章,于是在1912至1913年的冬季前往印度,心里琢磨著自己是否還寫得出小說。印度給了他極深的印象,他認為自己身上那褊狹保守、呆板土氣的成見被消除殆盡。不過,還是不可救藥。回來后,他開始著手創作一部有關印度的小說,但隨即陷入了困境,找不出如何解脫出來的方法。他私下里譴責自己虛弱無力,并琢磨起這么懶散的一個人,究竟有無權利批評為了謀生而勞動的大眾。他害怕倘若這樣下去,自己會變得十分古怪而不得人心。
隨后,1913年9月,他去拜訪愛德華·卡彭特,一位倡導純樸生活與具有高尚情操的同性愛之先知,并體驗到一次啟示。他本人在《結尾的札記》中描述了所發生的事。卡彭特的朋友喬治·梅里爾觸了觸他腰眼下面的部位。用他的話來說,觸覺從臀部上方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他的構思。就在那一瞬間,一部新穎的小說在他的頭腦里形成了。它涉及同性愛,給予三個中心人物以顯要地位,并且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結局。
他終于知道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多年來,《莫瑞斯》或是類似于《莫瑞斯》這樣的作品,一直在提出誕生的要求。他已經寫了幾篇以同性愛為主題的輕浮的短篇小說來寬慰自己。然而,這還不夠,盡管他并不因它們而害羞,也無意放棄它們。但當時磨煉與自我抑制還不夠到位。
現在,時機到了。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在想象中他敢于對自己做出保證:他相信同性愛是美好的。他需要義無反顧地肯定,這種愛可以使人變得高尚,并非導致人墮落。個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態”,那是社會的反常,它荒謬地對人類遺傳的這一極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認。
他心頭的郁悶消失了。他進入一種興奮狀態,立即坐下來寫作,不出三個月就完成了莫瑞斯的童年與劍橋之經歷的初稿。那時,他的熱忱遭到挫折。洛斯·迪金森[1]讀完他那些輕浮的短篇小說之一,感到震驚,引起反感,這使他心煩意亂到極點,盡管如此,他還是不屈不撓地寫下去。翌年4月,他受到更嚴重的打擊。在小說中,他濃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與休·O·梅瑞狄斯之間的友誼,但是梅瑞狄斯被示以手稿之后,似乎對它完全感到厭煩——不僅如此,他好像甚至不覺得自己這樣冷漠有什么關系。此次打擊使得福斯特考慮放棄這部小說。然而,這種情緒沒有持續多久,1914年7月,《莫瑞斯》脫稿。
他完全沒想過此書有出版的可能性。他認為“直到我本人去世,英國消亡”,這部作品是出版不了的。實際上,他原先僅僅打算為自己而寫。不過,他很快就開始拿給經過挑選的朋友們看,頭一個看到的是迪金森。迪金森覺得它很感動人,使福斯特非常寬慰。但是,在迪金森看來,那個快樂的結局太不自然了。福斯特本人也曉得這是此作差勁兒的部分,就著手予以改進(以后又修改多次)。他看得出毛病出在哪里,這關系到他寫此書的整個動機。“我要是把它(阿列克·斯卡德這部分)也化為塵埃或霧靄,那就更明智一些。”他寫信給迪金森說:“然而,給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實際生活所不提供的快樂,這誘惑簡直是不可抗拒。‘為什么不呢?’我一直這么想。‘稍微重新安排一下,運氣就好多了,’——但是,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讓作品能夠不朽的這一渴望,引導一位小說家在每一部作品接近末尾時談理論。死亡這樁事實是理論之外的唯一的不朽。也許我在《最漫長的旅程》中過分沉溺于死亡了。無論怎樣,我越來越不傾向于將主人公殺掉。”(1914年12月13日)
一兩個月后,他多少有些焦慮不安地把這部小說拿給交情較淺的朋友福雷斯特·里德看。里德不曾像福斯特所擔心的那樣感到驚愕。然而此作沒有真正合他的口味。他提出的異議促使福斯特進行更長的辯護。
“我的確想撥開神話那片薄霧,提出這些問題:神創造了男人和女人,不包括他們,而把克萊夫這樣一些未成熟的人排除在外……讓其處于‘性反常者’(這是個荒謬的詞,因為它假定他們是被賦予選擇之自由的。然而,咱們還是用它吧)狀態。由于社會那罪惡的愚昧無知,使得這些‘性反常者’對惡的傾向不均衡(我承認這一點)。他們究竟是跟正常人一樣好或壞,還是天生就這么壞呢?你像我似的,回答說他們是前者,然而你是勉勉強強這么回答的,我卻希望你充滿激情地回答:‘我這本書里的人,大致說來是好的,但是社會幾乎把他毀了。’他差點兒畢生過鬼鬼祟祟的日子,偷偷摸摸,戰戰兢兢,背著罪惡感的包袱。你說:‘倘若他沒遇上另一個像他這樣的人,會怎么樣呢?’真的,會怎么樣呢?不過,去責怪社會吧,別歸咎于莫瑞斯。即使是在一部小說里,當一個人得以過上自己所能過的最美好的生活時,應感謝才是!
“這把我引到另一個問題上來了……這種關系倘若把肉體也包括進去,到底對不對?對——在某些情況下。假若雙方都有這個需要,而且雙方的年齡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就是對的。我一向不去想這個問題,然而現在卻開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萊夫就不對,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對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則十分對。某些人之間,永遠都不對……
“在任何一場‘最后的審判’上,我都會為自己辯護說:‘我試圖將與生俱來的所有的斷片聯結起來,派上用場。’——唷,在《霍華德別業》中,這個題材已被耗盡了。莫瑞斯的斷片盡管比瑪嘉麗的稀少而奇異,卻跟她是同一個行業上的……”
光陰荏苒,他對各式各樣的朋友的反應做出回應,對此所作的評價隨之忽高忽低。有時候他確信自己做了“一樁絕對新穎的事,甚至面對希臘人亦然”。另外一些時候他疑慮重重——主要是小說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體上的快樂。“在藝術處理中,再也沒有比肉欲更執拗的了,”1920年,他寫信給西格弗里德·薩松[2]:“然而,我深信,非安排進去不可:事事都得安排進去。”1919年,他對艱難的最后部分進一步做了改動,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當大刀闊斧地予以修訂。一位讀者對結局[3]提出質疑,寫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啟航駛向阿根廷,隨后把臉朝英格蘭掉過去。情緒激昂,無所畏懼,一片模糊,驚心動魄,令人難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樣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為此發愁,于是增添了一節,從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懷抱中。
到了20世紀60年代,他母親以及絕大多數近親均已去世,社會上對性的問題之態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倘若他愿意的話,是可以出版這部小說的。朋友們確實提出過這個建議,然而他堅決地拒絕了。他知道這會導致永無休止的大驚小怪與喧鬧騷動。而且對他來說,此作已變得頗為遙遠了。他說,自己對獲得拯救、來自“某處”的援救者這個題目的興趣已經沒那么大了,他認為那是騙人的。人們可以相互幫助,但是他們并不像那樣彼此替對方做出決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兩位友人認為它已“過時”。他為自己死后出版此作做了周密的準備。但是他的最后的評論(親筆寫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嗎?”這部杰出而動人心弦的小說的讀者,沒有幾個會做出感到絲毫懷疑的答復。
P·N·費爾班克
1913年動筆
1914年完稿
獻給更幸福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