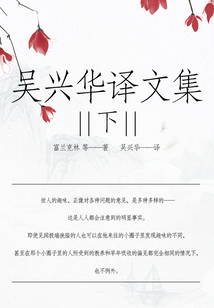
吳興華譯文集(下)
最新章節(jié)
- 第17章 朗費(fèi)羅:伊凡吉琳(選譯)
- 第16章 康拉德·艾肯:而在那高懸的園中——
- 第15章 司高脫詩(shī)鈔
- 第14章 里爾克詩(shī)選譯
- 第13章 但尼生詩(shī)鈔
- 第12章 穆?tīng)栐?shī)鈔
第1章 論趣味的標(biāo)準(zhǔn)
世人的趣味,正像對(duì)各種問(wèn)題的意見(jiàn),是多種多樣的——這是人人都會(huì)注意到的明顯事實(shí)。即使見(jiàn)聞極端狹隘的人也可以在他來(lái)往的小圈子里發(fā)現(xiàn)趣味的不同,甚至在那個(gè)小圈子里的人所受到的教養(yǎng)和早年吸收的偏見(jiàn)都完全相同的情況下,也不例外。至于那些能夠擴(kuò)大眼光縱觀異國(guó)和遠(yuǎn)古的人,對(duì)這方面的千歧百異齟齬矛盾就更會(huì)感到驚異了。我們往往把一切與自己的趣味和鑒賞力大相徑庭的看法貶斥為“野蠻”,但轉(zhuǎn)眼就發(fā)現(xiàn)別人也把同樣的貶詞加在我們身上。最后,就連最傲慢自信目空一切的人也會(huì)出乎意外地覺(jué)察到,各方面都是同樣自以為是,面對(duì)紛紜爭(zhēng)競(jìng)的好惡,不再敢肯定自己是一定正確的了。
雖說(shuō)這種趣味的差異是漫不經(jīng)心的觀察者也會(huì)注意到的,但只要仔細(xì)考慮一下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實(shí)際上的差異比看來(lái)還要大得多。人們對(duì)各種類(lèi)型的美和丑一般議論往往相同,而具體感受則互有歧異。每種語(yǔ)言里都有些表示譴責(zé)和表示稱(chēng)許的名詞;這些名詞在用同一語(yǔ)言的人們手里必然會(huì)得到一致的應(yīng)用。優(yōu)美、恰當(dāng)、簡(jiǎn)明、生動(dòng),這些是眾口交贊的;虛夸、造作、平庸、浮艷,這些是齊聲申斥的;但一遇到具體例子,批評(píng)家之間這種貌似一致的情況就消失了;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賦予同一說(shuō)法的意義是遠(yuǎn)不相同的。科學(xué)和理論問(wèn)題情況則恰恰相反:在那些領(lǐng)域里,人們意見(jiàn)的歧異往往是對(duì)一般,而不是對(duì)具體;往往看來(lái)懸殊,而其實(shí)不然。把名詞解說(shuō)清楚之后時(shí)常就沒(méi)有什么可爭(zhēng)的了,結(jié)果論辯雙方會(huì)驚愕地發(fā)現(xiàn)他們吵了半天其實(shí)意見(jiàn)是完全一致的。
有一派人認(rèn)為道德的基礎(chǔ)是感受而不是理智;他們傾向于把倫理學(xué)歸入前一類(lèi),堅(jiān)持人們對(duì)一切有關(guān)行為和風(fēng)尚問(wèn)題看法上的歧異實(shí)際上比看來(lái)還要大。顯而易見(jiàn),無(wú)論何時(shí)何地的作家都懂得贊揚(yáng)正義、仁慈、慷慨、慎重和誠(chéng)實(shí),并且譴責(zé)與之相反的各種品質(zhì)。就連以?shī)蕫傋x者想象力為主的詩(shī)人和其他文藝創(chuàng)作者,從荷馬一直到費(fèi)奈龍,也都教導(dǎo)相同的道德信條,稱(chēng)許和譴責(zé)相同的美德和惡習(xí)。依照一般解釋?zhuān)@種一致性是在純理智影響下產(chǎn)生的;因?yàn)槔碇悄茉谝磺腥诵睦锱囵B(yǎng)對(duì)那些道德品質(zhì)的類(lèi)似感受,從而就消除了抽象科學(xué)容易引起的爭(zhēng)辯。在這種一致性確屬真實(shí)的限度內(nèi),我們不妨承認(rèn)上述解釋足以令人滿意。但是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看到在道德方面這種表面上的協(xié)調(diào)有一部分也是語(yǔ)言本質(zhì)所造成的結(jié)果。“美德”這個(gè)詞,不管在不同語(yǔ)言里用什么形式表現(xiàn),總歸意味著稱(chēng)許,“惡習(xí)”總歸意味著譴責(zé)。除非一個(gè)人硬要犯大不韙,顛倒黑白,他就絕不會(huì)把普通人都理解為好意的詞用作惡意,或者用明明是表示責(zé)備的詞來(lái)表示贊揚(yáng)。荷馬偶爾也作些一般性的道德議論,對(duì)這些議論的內(nèi)容,誰(shuí)也不會(huì)有所非難。但顯然當(dāng)他描繪具體人物的行為,企圖說(shuō)明阿喀琉斯如何英勇,俄底修斯如何足智多謀的時(shí)候,他使前者所透露的兇狠和后者所表現(xiàn)的奸刁欺詐都是費(fèi)奈龍所決不會(huì)容許的。荷馬筆下的智多星俄底修斯仿佛天生就喜歡說(shuō)謊和欺騙,常常在既無(wú)必要也無(wú)好處的場(chǎng)合也要施用那套伎倆;費(fèi)奈龍所塑造的太雷馬克(俄底修斯的兒子)就更為潔身自好,他寧可使自己遭受臨近目前的險(xiǎn)難,也絕不肯離開(kāi)最嚴(yán)格的真理和誠(chéng)實(shí)的道路。
把《可蘭經(jīng)》奉為神明的人們強(qiáng)調(diào)在那本書(shū)里有不少極有價(jià)值的道德條文。但是我想在阿拉伯語(yǔ)言里那些和英語(yǔ)的“無(wú)私”、“公正”、“節(jié)制”、“溫和”、“仁愛(ài)”等相當(dāng)?shù)脑~,由于經(jīng)久運(yùn)用,約定俗成,一定也總是具有好意;如果提到這些詞,不加以贊揚(yáng)和肯定反而給予其他評(píng)語(yǔ),那不僅是對(duì)道德,就連対語(yǔ)言,也可以說(shuō)是完全愚魯無(wú)知。但是假使我們想知道那位先知是否有正確的道德感情,只需讀一遍書(shū)中的敘事部分就夠了。
所以說(shuō)倫理學(xué)上的一般議論,即使正確,價(jià)值也很微小。頌揚(yáng)任何美德其實(shí)只不過(guò)是發(fā)揮原詞的含義。最初創(chuàng)造“仁愛(ài)”這個(gè)詞并且用它來(lái)表示好意的民族,比起那些只會(huì)在著作里高談“待人仁恕”的自封的立法家和先知,應(yīng)該說(shuō)把這番道理闡明得更為清晰;至于效果更是不可同日而語(yǔ)了。本來(lái),在全部語(yǔ)言當(dāng)中最不容易受到歪曲和誤解的正是那些除了其他意義之外還含有一定程度褒貶含義的詞。
我們想找到一種“趣味的標(biāo)準(zhǔn)”,一種足以協(xié)調(diào)人們不同感受的規(guī)律,這是很自然的;至少,我們希望能有一個(gè)定論,可以使我們證實(shí)一種感受,否定另一種感受。
然而有一派哲學(xué)卻認(rèn)為我們這種企圖全是妄想,因?yàn)椤叭の兜臉?biāo)準(zhǔn)”永遠(yuǎn)無(wú)法找到。據(jù)那些哲學(xué)家說(shuō),判斷和感受截然不同,一切感受都是正確的,因?yàn)楦惺芗兒跻宰约簽闇?zhǔn);只要一個(gè)人意識(shí)到有所反應(yīng),那就是真實(shí)的。但是理智上的決定則不能認(rèn)為都是正確的,因?yàn)樗鼈冃枰酝馕铩嗉磳?shí)際情況——為準(zhǔn);這樣一衡量,顯然它們不可能都符合。假使不同的人對(duì)同一事物有一千種不同意見(jiàn),其中只有一種,也只能有一種,是正確的,真實(shí)的;唯一困難在于如何找出并且認(rèn)識(shí)這種正確意見(jiàn)。相反,同一事物引起的不同感受則都是正確的:因?yàn)楦惺懿⒉惑w現(xiàn)任何事物的內(nèi)在屬性;它只標(biāo)志事物與人的心靈(器官或功能)中間的一種合拍狀態(tài)或聯(lián)系;如果這種合拍狀態(tài)實(shí)際不存在,那么根本就沒(méi)有產(chǎn)生任何感受的可能。美就不是客觀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的內(nèi)在屬性,它只存在于鑒賞者的心里;不同的心會(huì)看到不同的美;每個(gè)人只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自己的感受,不應(yīng)當(dāng)企圖糾正他人的感受。想發(fā)現(xiàn)真正的美或丑,就和妄圖發(fā)現(xiàn)真正的甜或苦一樣,純粹是徒勞無(wú)功的探討。根據(jù)不同的感官,同一事物可以既是甜的,也是苦的;那句流行的諺語(yǔ)早就正確地教導(dǎo)我們:關(guān)于口味問(wèn)題不必作無(wú)謂的爭(zhēng)論。把這個(gè)道理從對(duì)飲食的“口味”引申到對(duì)精神事物的“趣味”是很自然的,甚至極為必要的;這樣一來(lái),我們就發(fā)現(xiàn)常識(shí)盡管在多數(shù)情況下與哲學(xué)(特別是懷疑派哲學(xué))相互抵觸,至少在這問(wèn)題上,二者竟得出一致的結(jié)論。
雖然上述道理,由于成為諺語(yǔ),仿佛已經(jīng)獲得常識(shí)的認(rèn)可;但此外還有一種常識(shí)的表現(xiàn)卻是肯定與它截然對(duì)立,至少是足以修正和制約它的。誰(shuí)要是硬說(shuō)奧基爾比和密爾頓、本揚(yáng)和艾迪生在天才和優(yōu)雅方面完全均等,人們就一定會(huì)認(rèn)為他是在大發(fā)謬論,把丘垤說(shuō)成和山陵一樣高,池沼說(shuō)成和海洋一樣廣。即使真有人偏嗜前兩位作家,他們的“趣味”也不會(huì)得到重視;我們將毫不遲疑地宣稱(chēng)像那樣打著批評(píng)家招牌的人的感受是荒唐而不值一笑的。遇到這種場(chǎng)合,我們就把“趣味天生平等”的原則丟在腦后了;如果相互比較的事物原來(lái)近乎平等,我們還可以承認(rèn)那條原則;當(dāng)其中的差距是如此巨大的時(shí)候,它就成為不負(fù)責(zé)任的怪論,甚至顯而易見(jiàn)的胡說(shuō)了。
寫(xiě)作規(guī)律都不是靠因果推斷制訂出來(lái)的,都不能算理性的抽象結(jié)論——這點(diǎn)只需與那些永恒不變的觀念形態(tài)和關(guān)系比較一下就不言自明,寫(xiě)作規(guī)律的基礎(chǔ)也就是一切實(shí)用科學(xué)的基礎(chǔ)——經(jīng)驗(yàn);它們不過(guò)是根據(jù)在不同國(guó)家不同時(shí)代都能給人以快感的作品總結(jié)出來(lái)的普遍性看法。詩(shī)歌中甚至雄辯中的美常常是依靠捏造和虛構(gòu)、依靠夸張、譬喻和使文詞違反天生意義的歪曲和濫用。但若想制止這種想象力的奔放,叫一切表現(xiàn)手法符合幾何真理和精確性,那就和批評(píng)法則完全背道而馳;理由是普遍經(jīng)驗(yàn)早已證明這樣作法的結(jié)果只會(huì)產(chǎn)生最枯燥的令人起厭的作品。因此詩(shī)歌永遠(yuǎn)不能服從精確的真理,但它同時(shí)必須受到藝術(shù)規(guī)律的制約,這些規(guī)律是要靠作家的天才和觀察力來(lái)發(fā)現(xiàn)的。的確,有些不拘細(xì)節(jié),不守繩墨的作家也可以給人快感;但他們絕不是因?yàn)槠茐牧艘?guī)律或定式才給人快感;相反,是盡管破壞了規(guī)律或定式而仍然給人快感,他們一定有其他符合公正批評(píng)的優(yōu)點(diǎn),瑜足以掩瑕,因此才能使讀者感到滿意,從而把由那些缺陷而產(chǎn)生的厭惡心情壓抑下去。阿里奧斯多是個(gè)討人歡喜的作家,但那不是因?yàn)樗麘{空編造些牛鬼蛇神,把嚴(yán)肅風(fēng)格和喜劇風(fēng)格亂扯在一起,故事布局不講先后呼應(yīng),時(shí)常打斷敘述、節(jié)外生枝。他的魅力在于語(yǔ)言明朗生動(dòng)、才思噴涌變幻,善于摹寫(xiě)感情,特別是歡笑和戀愛(ài)的感情。上面那些毛病雖然減弱了我們的快感,卻不能完全把它抵消。即使退一步說(shuō),假定我們的快感果真是由于上文認(rèn)為是毛病的那些部分所造成的;這也不足以證明一般批評(píng)都是毫無(wú)用處。它只能證明把上述各點(diǎn)列為毛病并且斷言它們永遠(yuǎn)應(yīng)該受到譴責(zé)的具體批評(píng)條例不能成立。既是給人快感就不能算毛病,不管快感的產(chǎn)生是如何突如其來(lái),難以解釋。
但是藝術(shù)的一般規(guī)律雖然都不過(guò)是根據(jù)經(jīng)驗(yàn)和對(duì)人類(lèi)普遍感受的觀察;我們卻不可因此以為在所有情況下人的反應(yīng)都自然會(huì)與這些規(guī)律吻合。有些較細(xì)致的感情是非常嬌嫩,非常柔脆的;需要在許多有利條件的結(jié)合之下才能根據(jù)普遍既定的原則自在發(fā)揮,精確無(wú)誤。它們仿佛是機(jī)器里的細(xì)小發(fā)條,只要有些微外部干擾或內(nèi)部振蕩,開(kāi)動(dòng)就會(huì)受阻,使全盤(pán)機(jī)器因而不能操作。我們?nèi)粢鬟@方面的實(shí)驗(yàn),借以鑒定任何美或丑,一定先要選擇合宜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使想象處于一種適當(dāng)?shù)沫h(huán)境和狀態(tài),心情要平靜,思想要集中,注意觀察對(duì)象。這些條件當(dāng)中只要有一項(xiàng)不具備,實(shí)驗(yàn)結(jié)果就會(huì)錯(cuò)誤,我們也就無(wú)法判斷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美。至少,自然在形體和感受之間所建立的關(guān)系就會(huì)因此變得模糊不清,需要更大的準(zhǔn)確性才能發(fā)現(xiàn)和認(rèn)識(shí)。我們?nèi)粝氪_定它的作用,不能只根據(jù)個(gè)別的美所產(chǎn)生的效果,主要還應(yīng)該根據(jù)那些歷盡一切風(fēng)氣和時(shí)髦的變化,一切無(wú)知和嫉妒的誤解而仍然存留下來(lái)的作品在我們心中喚起的經(jīng)久的愛(ài)慕。
同一個(gè)荷馬,兩千年前在雅典和羅馬受人歡迎,今天在巴黎和倫敦還被人喜愛(ài)。地域、政體、宗教和語(yǔ)言方面的千變?nèi)f化都不能使他的榮譽(yù)受損。偶爾一個(gè)糟糕的詩(shī)人或演說(shuō)家,以權(quán)威和偏見(jiàn)作靠山,也會(huì)風(fēng)行一時(shí)。但他的名氣絕不能普遍或長(zhǎng)久。后世或外國(guó)讀者一仔細(xì)考察他的作品,虛幻的魔法就消散了,使他的毛病呈現(xiàn)出本來(lái)面目。真正的天才情況恰恰相反,作品歷時(shí)愈久,傳播愈廣,愈能得到衷心的敬佩。在一個(gè)狹隘的圈子里,羨妒之情往往會(huì)占突出地位;甚至由于熟識(shí)他本人也會(huì)削弱應(yīng)當(dāng)給予他創(chuàng)作的贊賞。但是一旦這些障礙沒(méi)有了,本來(lái)可以動(dòng)人心魄的優(yōu)點(diǎn)就會(huì)立刻發(fā)揮力量;它們?cè)谧x者中間的威信將會(huì)與世界共垂不朽。
由此可見(jiàn),盡管趣味仿佛是變化多端,難以捉摸,終歸還有些普遍性的褒貶原則;這些原則對(duì)一切人類(lèi)的心靈感受所起的作用是經(jīng)過(guò)仔細(xì)探索可以找到的。按照人類(lèi)內(nèi)心結(jié)構(gòu)的原來(lái)?xiàng)l件,某些形式或品質(zhì)應(yīng)該能引起快感,其他一些引起反感;如果遇到某個(gè)場(chǎng)合沒(méi)有能造成預(yù)期的效果,那就是因?yàn)槠鞴俦旧碛忻』蛉毕荨0l(fā)高燒的人不會(huì)堅(jiān)持自己的舌頭還能決定食物的味道;害黃疸病的人也不會(huì)硬要對(duì)顏色作最后的判斷。一切動(dòng)物都有健全和失調(diào)兩種狀態(tài),只有前一種狀態(tài)能給我們提供一個(gè)趣味和感受的真實(shí)標(biāo)準(zhǔn)。在器官健全的前提下,如果人們的感受完全或者基本相同,我們就能因之得出“至美”的概念。這正和顏色的情況一樣,雖然一般認(rèn)為顏色只不過(guò)是官覺(jué)的幻象,我們還是作出如下的規(guī)定:只有事物在白晝中間對(duì)一個(gè)眼力健全的人所呈現(xiàn)出的才可稱(chēng)為是它正確真實(shí)的顏色。
內(nèi)心器官有許多不斷發(fā)生的毛病,足以抑止或削弱那些指導(dǎo)我們美丑感受的普通原則,使之不能起正常作用。雖說(shuō)某些對(duì)象,由于人類(lèi)內(nèi)心的特殊結(jié)構(gòu),天然能夠引起快感,我們不能因此期望每個(gè)人都會(huì)同樣意識(shí)到這種快感。往往有些特殊事件或場(chǎng)合會(huì)把對(duì)象籠罩在虛幻的光亮里,或是使我們的想象不能感受或覺(jué)察到真實(shí)的光亮。
多數(shù)人所以缺乏對(duì)美的正確感受,最顯著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象力不夠敏感,而這種敏感正是傳達(dá)較細(xì)致的情緒所必不可少的。每個(gè)人都自稱(chēng)具有這種敏感,談起來(lái)滔滔不絕,想把各式各樣的趣味和感受都?xì)w納到這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之下。但是既然本文的宗旨就在對(duì)這個(gè)感受問(wèn)題作出一定程度的理性解釋?zhuān)o所謂“敏感”下一個(gè)比歷來(lái)各家所作出的更準(zhǔn)確的定義應(yīng)該說(shuō)是必需的。我們不必乞靈于任何高奧艱深的哲學(xué),只要引用《堂·吉訶德》里面一段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行了。
桑科對(duì)那位大鼻子的隨從說(shuō):“我自稱(chēng)精于品酒,這絕不是瞎吹。這是我們家族世代相傳的本領(lǐng)。有一次我的兩個(gè)親戚被人叫去品嘗一桶酒,據(jù)說(shuō)是很好的上等酒,年代既久,又是名牌。頭一個(gè)嘗了以后,咂了咂嘴,經(jīng)過(guò)一番仔細(xì)考慮說(shuō):酒倒是不錯(cuò),可惜他嘗出里面有那么一點(diǎn)皮子味。第二個(gè)同樣表演了一番,也說(shuō)酒是好酒,但他可以很容易地辨識(shí)出一股鐵味,這是美中不足。你絕想象不到他倆的話受到別人多大的挖苦。可是最后笑的是誰(shuí)呢?等到把桶倒干了之后,桶底果然有一把舊鑰匙,上面掛著一根皮條。”
由于對(duì)飲食的口味對(duì)精神事物的趣味非常相似,這個(gè)故事就很能說(shuō)明問(wèn)題。盡管美丑,比起甘苦來(lái),可以更肯定地說(shuō)不是事物的內(nèi)在屬性,而完全屬于內(nèi)部或外部的感受范圍;我們總還得承認(rèn)對(duì)象中有些東西是天然適于喚起上述反應(yīng)的。但這些東西可能占的比重很小,或者彼此混雜糾纏在一起;結(jié)果我們的趣味往往不能感到過(guò)于微小的東西,或者在混亂呈現(xiàn)的狀態(tài)下把每種個(gè)別的味道都辨別出來(lái)。如果器官細(xì)致到連毫發(fā)異質(zhì)也不放過(guò),精密到足以辨別混合物中的一切成分:我們就稱(chēng)之為口味敏感,不管是按其用于飲食的原義還是引申義都是一樣。在這里關(guān)于美的一般規(guī)律就能起作用了,因?yàn)樗鼈兪菑囊延卸ㄕ摰姆独陀^察一些集中突出體現(xiàn)快感和反感的對(duì)象里得出來(lái)的,當(dāng)同樣品質(zhì)散見(jiàn)于一篇首尾完整的文章里,所占比重又很小時(shí),有些人的器官就不能清楚地起快慰或嫌惡的反應(yīng),像這樣的人我們就不該允許他給自己敏感的稱(chēng)號(hào)。把這些一般規(guī)律或創(chuàng)作的公認(rèn)楷模拿出來(lái)就可以比作找到那把拴皮帶的鑰匙;桑科的親戚所以能夠證明自己正確,使那些嗤笑他們的所謂“行家”大受其窘,也就是因?yàn)檎业搅四前谚€匙。當(dāng)然,即使不把酒桶倒干,那兩個(gè)親戚的“口味”還不失為敏感,譏笑他們的人的“口味”還是遲鈍糊涂,但想要說(shuō)服所有在旁邊看熱鬧的群眾前者確比后者高明,就困難得多了。同樣,雖然寫(xiě)作的美還沒(méi)有條理化,沒(méi)有歸納成為一系列普遍規(guī)律,雖然公認(rèn)完美無(wú)缺的典范還沒(méi)有找到;趣味有高有低,一個(gè)人的鑒賞能力比另一個(gè)人強(qiáng),這還是不可抹殺的事實(shí),但想叫不對(duì)頭的批評(píng)家噤若寒蟬卻不那么容易,因?yàn)樗麧M可以堅(jiān)持以自己的感受為準(zhǔn),拒絕接受對(duì)方的判斷。只有當(dāng)我們拿出一條公認(rèn)的藝術(shù)法則給他看,并且用一些根據(jù)他自己的趣味他也承認(rèn)能夠依照這條法則發(fā)生作用的例子來(lái)說(shuō)明該法則,然后再證明,雖然他在當(dāng)前討論的對(duì)象里覺(jué)察感受不到任何反應(yīng),同樣的法則其實(shí)還在起作用——只有在這時(shí),他才會(huì)被迫承認(rèn)(總的講來(lái))毛病在于他自己,因?yàn)樗狈δ欠N能夠使他在任何作品、任何言論中辨識(shí)出一切美和丑的必不可少的敏感。
如果某種機(jī)能或官覺(jué)能夠精確地感到最微小的對(duì)象,不讓任何東西逃脫它的注意和觀察,我們就承認(rèn)它已經(jīng)發(fā)達(dá)到完美境界。眼睛所看到的事物越小,視覺(jué)器官就越好,或者說(shuō)構(gòu)筑得越復(fù)雜精密。要測(cè)驗(yàn)舌頭的鑒別力不能靠強(qiáng)烈的“味道”,應(yīng)該把各微細(xì)的“作料”混合起來(lái),使得份量雖少并且攙混在一起,我們?nèi)杂锌赡鼙鎰e其中每一部分。同樣,迅速而敏銳的審美感也正標(biāo)志著精神趣味發(fā)達(dá)到了完美境界。只要一個(gè)人懷疑自己把某篇文章里的優(yōu)點(diǎn)或缺點(diǎn)漏過(guò)去了,他就應(yīng)該明白自己的趣味還有問(wèn)題。在這點(diǎn)上,官覺(jué)或感覺(jué)的完美和為人的完美是統(tǒng)一的,一個(gè)人如果舌頭十分敏感常常會(huì)不止給自己,也給自己的朋友惹來(lái)許多麻煩。但對(duì)才華或美的敏感卻永遠(yuǎn)是一種令人向往的品質(zhì);因?yàn)樗侨祟?lèi)天性所能享受的一切最高尚而純潔的歡樂(lè)的泉源。關(guān)于這點(diǎn),全人類(lèi)的看法完全一致。只要你能確定某人有敏感的口味,它就一定能博得贊許。而最好的確定方法就是把不同國(guó)家不同時(shí)代的共同經(jīng)驗(yàn)所承認(rèn)的模范和準(zhǔn)則當(dāng)作衡量尺度。
還需要指出:雖然人和人之間敏感的程度可以差異很大,要想提高或改善這方面的能力最好的辦法無(wú)過(guò)于在一門(mén)特定的藝術(shù)領(lǐng)域里不斷訓(xùn)練,不斷觀察和鑒賞一種特定類(lèi)型的美。任何對(duì)象初次出現(xiàn)在眼前或想象當(dāng)中時(shí),引起的感受總不免是糢糊的、混亂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無(wú)法對(duì)它們的美或丑作出判斷。我們的趣味感覺(jué)不到對(duì)象里的各種優(yōu)點(diǎn),更不要說(shuō)辨別每種優(yōu)點(diǎn)的特性,確定它的質(zhì)量和程度了。假使能就整體作一個(gè)大致的評(píng)語(yǔ):是美還是丑,這已經(jīng)是至矣盡矣;而就連這樣一個(gè)判斷,一個(gè)人如果缺乏訓(xùn)練,作起來(lái)也會(huì)是躊躇的,有保留的。但在他關(guān)于這種對(duì)象獲得一定經(jīng)驗(yàn)之后,他的感覺(jué)就會(huì)更精細(xì)更深入了。他將會(huì)不止看到每一部分的美和丑,而且能分別不同類(lèi)型,各給以適如其分的褒貶。在整個(gè)觀察對(duì)象的過(guò)程中,他的感受是明晰肯定的;對(duì)每一部分應(yīng)該喚起的快感或反感究竟到何種程度,屬于何種類(lèi)型,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本來(lái)仿佛遮掩著對(duì)象的迷霧消散了,器官由于經(jīng)常運(yùn)用也就日趨完美,以至最后可以判斷一切作品的優(yōu)點(diǎn),不必害怕會(huì)犯錯(cuò)誤。一句話,完成任何作品和判斷任何作品所需的巧妙和敏捷,都只有通過(guò)訓(xùn)練才能獲得。
由于訓(xùn)練對(duì)審美感極端有利,我們?cè)谠u(píng)論任何重要作品之前應(yīng)該永不例外地把它一讀再讀,仔細(xì)地全神貫注地從不同角度對(duì)它進(jìn)行觀察。初讀任何作品,心情上總不免有些忙亂,從而使對(duì)美的真實(shí)感受到干擾。我們會(huì)看不到各部分中間的聯(lián)系,分辨不清風(fēng)格變化的真正性質(zhì);不同的優(yōu)缺點(diǎn)仿佛糅雜在一起,糢糊地呈現(xiàn)在我們想象力當(dāng)中。還不用說(shuō)另有一種浮淺涂飾的美,初看固然叫人喜歡,經(jīng)過(guò)考慮后就發(fā)現(xiàn)和理性或激情的正常表達(dá)方式完全不相容,因此使我們的口味厭膩——這時(shí)我們就會(huì)鄙棄地把它丟開(kāi),或至少大大降低對(duì)它的估價(jià)。
只要我們不斷堅(jiān)持任何審美方面的訓(xùn)練,總不免要常常在不同類(lèi)型和程度的完善中間進(jìn)行比較,并估計(jì)其分量上的差異。一個(gè)人如果沒(méi)有機(jī)會(huì)比較不同類(lèi)型的美,就根本沒(méi)有資格對(duì)任何對(duì)象下斷語(yǔ)。只有通過(guò)比較,我們才能確定褒貶的言詞,才能知道怎樣褒貶得恰如其分。信筆亂涂的畫(huà)也會(huì)有些鮮艷彩色和大致類(lèi)似之處,在有限的意義下講來(lái),也可以算美,讓一個(gè)種地的或印第安人看見(jiàn)了說(shuō)不定會(huì)拍手叫絕。最下流的小調(diào)里也會(huì)有和諧自然的片斷;只有熟悉更高級(jí)的美的人才能肯定指出它的調(diào)子刺耳,詞句庸俗。一個(gè)習(xí)慣于美的最高形式的人看到極端低級(jí)的美一定會(huì)感覺(jué)痛苦;也正是由于這個(gè)原因,我們才稱(chēng)之為丑。但既然我們每個(gè)人都自然會(huì)以為自己所知道的最完整無(wú)憾的對(duì)象就代表盡美盡善的頂峰,應(yīng)該得到最高的稱(chēng)許;那么真正有資格估計(jì)眼前對(duì)象的優(yōu)點(diǎn)并在歷代天才的產(chǎn)物當(dāng)中給予它以適當(dāng)位置的,應(yīng)該只是那些對(duì)不同時(shí)代不同國(guó)家交口贊美的各個(gè)作品經(jīng)常進(jìn)行觀察、硏究和比較的人。
但是一個(gè)打算很好地完成這樁任務(wù)的批評(píng)家還必須能夠擺脫一切偏見(jiàn),除了研究放在眼前的對(duì)象之外,不作任何其他考慮。應(yīng)該指出:一切藝術(shù)作品為了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效果,必須從一定的角度來(lái)觀察。如果觀察者的立足點(diǎn)(實(shí)際的或想象的)和作品所要求的不一致,他對(duì)作品就無(wú)法欣賞。演說(shuō)家面對(duì)的是一些特定的聽(tīng)眾,他一定要照顧到他們特有的脾氣、喜好、看法、感情和偏見(jiàn),不然就休想左右他們的決定,燃起他們的熱情。甚至說(shuō)不定他們會(huì)對(duì)他抱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嫌忌,那么對(duì)這個(gè)不利條件(不管是如何謬妄無(wú)理),他也不能忽視;在談到正題之前,總得說(shuō)些使他們心平氣和的話,爭(zhēng)取他們的好感。后世或異國(guó)的批評(píng)家在閱讀他的演說(shuō)時(shí),只有把自己放在和當(dāng)時(shí)聽(tīng)眾相同的立足點(diǎn)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同樣,我和某作家可能是敵或友,但在閱讀他獻(xiàn)給公眾的作品時(shí),一定要拋棄這種立足點(diǎn),把自己想作一般群眾,如果可能的話,忘掉我“個(gè)人”和我的特殊情況。聽(tīng)任偏見(jiàn)驅(qū)使的人就不符合這個(gè)條件;他總是死抱住自己原來(lái)的立足點(diǎn),不肯換到作品所要求的角度。假使原作品的對(duì)象是不同時(shí)代不同國(guó)度的人,他對(duì)他們的特殊看法和偏見(jiàn)也毫不考慮;相反,他一腦子裝滿的全是自己這個(gè)時(shí)代和國(guó)家的習(xí)俗,從而就貿(mào)然譴責(zé)原來(lái)作品所針對(duì)的讀者認(rèn)為是佳妙的東西。假使作品是面對(duì)公眾的,他從不肯放寬自己的眼界,忘掉自己作為敵、友、競(jìng)爭(zhēng)者或評(píng)注家的個(gè)人利益,這樣一來(lái),他的感受就變質(zhì)了;原來(lái)如果給自己的想象以適當(dāng)推動(dòng),能夠暫時(shí)忘記自己,對(duì)美和丑應(yīng)該作出的反應(yīng),現(xiàn)在也作不到了。因此,他的趣味顯然是離開(kāi)了真實(shí)的標(biāo)準(zhǔn),結(jié)果也就不能具有任何權(quán)威的分量。
在一切訴諸理智的問(wèn)題上,偏見(jiàn)對(duì)審判極為有害,足以敗壞一切智力活動(dòng),這點(diǎn)是眾所周知的。其實(shí),它對(duì)高尚的趣味也同樣有害,同樣足以敗壞我們的審美感。必須有高明的見(jiàn)識(shí)才能抑止偏見(jiàn),不讓它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發(fā)生作用。因此在這個(gè)問(wèn)題上(正像在許多其他問(wèn)題上一樣)理性盡管不是趣味的基本組成部分,對(duì)趣味的正確運(yùn)用卻是不可缺少的指導(dǎo)。在所有崇高的天才作品當(dāng)中,各部分總是緊密聯(lián)系和吻合的;一個(gè)人的思想若是不夠廣闊,不能容納所有部分,彼此比較,以便發(fā)現(xiàn)整體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當(dāng)然就談不上感受其中的優(yōu)點(diǎn)或缺點(diǎn)。其次,每個(gè)藝術(shù)作品又都有一個(gè)特別為自己規(guī)定的目的或目標(biāo),判斷作品完美的程度應(yīng)該以它達(dá)到目標(biāo)的程度為準(zhǔn)。雄辯的目標(biāo)是說(shuō)服,歷史的目標(biāo)是教導(dǎo),詩(shī)歌的目標(biāo)是用移情動(dòng)魄的手段給人快感。在閱讀任何作品的時(shí)候,我們心目中一定要經(jīng)常保持著它的目標(biāo);同時(shí)判斷所采用的手段對(duì)達(dá)到目標(biāo)是否合適。此外,各種類(lèi)型的作品(包括詩(shī)歌在內(nèi))其實(shí)都不過(guò)是一系列命題和推斷;當(dāng)然這些命題和推斷有時(shí)并不是最科學(xué)最精確的,但至少得能說(shuō)得通,不管是怎樣經(jīng)過(guò)了想象的加工和裝點(diǎn)。悲劇和史詩(shī)里的人物推斷、思考、決定和行動(dòng)的方式應(yīng)該符合他們的性格和處境;像這樣一樁細(xì)致的工作,除了需要正確趣味和才華之外,如果缺乏判斷力,也絕無(wú)成功的希望。最后,我們當(dāng)然都知道:有助于提高理性活動(dòng)的各種因素,像官能完善、思維清晰、區(qū)別精確、感受靈活等對(duì)正確趣味的應(yīng)用也是同樣必需和不可分割的。一個(gè)見(jiàn)識(shí)高明同時(shí)對(duì)某門(mén)藝術(shù)又有經(jīng)驗(yàn)的人竟然不能判斷那種藝術(shù)的美,這是絕無(wú)僅有的事:趣味高尚而智力庸劣的現(xiàn)象也是同樣少見(jiàn)。
因此雖然趣味的原則是有普遍意義的,完全(或基本上)可以說(shu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真正有資格對(duì)任何藝術(shù)作品進(jìn)行判斷并且把自己的感受樹(shù)立為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人還是不多。內(nèi)心感官很難發(fā)展到完美狀態(tài),使上述的一般原則可以充分發(fā)揮作用,并且喚起與那些原則相應(yīng)的感覺(jué)。它們不是本來(lái)有缺陷,就是一時(shí)發(fā)生了什么毛病;因而所能激起的感受只能說(shuō)是錯(cuò)誤的。缺少敏感的批評(píng)家往往是隨意論斷,不作區(qū)分,只著眼于對(duì)象中那些比較粗陋顯著的品質(zhì);細(xì)致一些的筆觸他就一眼看過(guò),視而不見(jiàn)。如果缺乏訓(xùn)練,他的評(píng)語(yǔ)又會(huì)有混亂和遲疑的弊病。不運(yùn)用比較的結(jié)果會(huì)使他對(duì)淺薄可哂、其實(shí)應(yīng)該算作缺陷的“美”佩服得五體投地。偏見(jiàn)的影響會(huì)敗壞他的自然感受。沒(méi)有高明的見(jiàn)識(shí),他就不能看到在一切美當(dāng)中最優(yōu)越的應(yīng)居首位的布局和推斷的美。大多數(shù)人總不免要犯以上幾種毛病中的一種;因此即使在風(fēng)氣最優(yōu)雅的時(shí)代能對(duì)高級(jí)藝術(shù)作出正確判斷的人也是極少見(jiàn)的:只有卓越的智力加上敏銳的感受,由于訓(xùn)練而得到改進(jìn),通過(guò)比較而進(jìn)一歩完善,最后還清除了一切偏見(jiàn)——只有這樣的批評(píng)家對(duì)上述稱(chēng)號(hào)才能當(dāng)之無(wú)愧。這類(lèi)批評(píng)家,不管在哪里找到,如果彼此意見(jiàn)符合,那就是趣味和美的真實(shí)標(biāo)準(zhǔn)。
但是到哪里去找這樣的批評(píng)家呢?他們有什么可以辨識(shí)的特征呢?怎樣能區(qū)別真?zhèn)危姑芭普卟荒転E竽充數(shù)呢?這些問(wèn)題相當(dāng)使人為難,乍一看仿佛我們?nèi)闹髦季驮谙霐[脫的疑惑如今又再一度降臨到我們頭上了。
不過(guò)只要認(rèn)真考慮,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些是事實(shí)而不是感受的問(wèn)題。某人是否有高超的見(jiàn)識(shí)、敏銳的想象、不受偏見(jiàn)的沾染——這往往值得爭(zhēng)辯;意見(jiàn)紛歧各持一說(shuō),勢(shì)所難免。但這樣一個(gè)人是難能可貴應(yīng)受尊敬的——對(duì)這一點(diǎn)則全人類(lèi)的看法絕無(wú)二致。遇到懷疑爭(zhēng)競(jìng)的時(shí)候,我們只能采取處理一切理性爭(zhēng)端的辦法:每一方面都要盡量舉出自己所能想到的最有力的論據(jù);都要承認(rèn)的確存在一個(gè)真實(shí)肯定的標(biāo)準(zhǔn)——這里指的是實(shí)際的客觀存在;都要容許別人在訴諸同一標(biāo)準(zhǔn)時(shí)和自己的看法有所差異。如果我們已經(jīng)證明人的趣味有高有低,并非均等;證明通過(guò)公眾輿論的承認(rèn),某些人(不管實(shí)際找到他們是如何困難)可以具有壓倒其他人的權(quán)威——那么這對(duì)本文要說(shuō)明的問(wèn)題已經(jīng)是足夠了。
實(shí)際上,即以發(fā)現(xiàn)具體的趣味標(biāo)準(zhǔn)而論,困難也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大。盡管我們從理論上只承認(rèn)科學(xué)有明確的是非而感受沒(méi)有,但實(shí)踐證明前者常常比后者更難確定。抽象的哲學(xué)論點(diǎn),深?yuàn)W的神學(xué)體系,在某個(gè)時(shí)期可能風(fēng)靡一時(shí);隨后一個(gè)時(shí)期立刻就煙消云散了。它們的謬誤一旦受到揭發(fā),其他論點(diǎn)和體系就會(huì)起而代之,等到又有新論點(diǎn)和新體系來(lái)到,這些又得讓位。看來(lái)這些所謂科學(xué)的定論反而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容易隨偶然的風(fēng)氣而轉(zhuǎn)移,雄辯和詩(shī)歌的美則完全兩樣。對(duì)感情和自然的恰當(dāng)描繪經(jīng)過(guò)一段短短的時(shí)期就一定能獲得公眾的贊賞,而這種贊賞一旦獲得,是永不會(huì)失去的。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伊壁鳩魯和笛卡爾不妨新陳代謝,此起彼滅;但臺(tái)倫斯和維吉爾則能永遠(yuǎn)地不容爭(zhēng)論地掌握人類(lèi)的心靈。西塞羅的抽象哲學(xué)早就沒(méi)有價(jià)值了:但他的雄辯的力量至今仍受到我們的嘆賞。
不錯(cuò),趣味敏感的人確實(shí)很少,但由于他們見(jiàn)解高明、才能出眾,在社會(huì)里也很容易辨識(shí)出來(lái)。他們所受到的普遍推奉使他們給予任何天才作品的贊語(yǔ)能夠廣泛傳播,在群眾中占據(jù)優(yōu)勢(shì)。許多人,如果只依靠自己,美感就非常薄弱模糊;但一旦經(jīng)人指出,不管是怎樣的神來(lái)之筆,他們也都能欣賞。貨真價(jià)實(shí)的詩(shī)人或雄辯家每獲得一個(gè)愛(ài)好者,就會(huì)通過(guò)他爭(zhēng)取到更多新的愛(ài)好者。盡管各式各樣的偏見(jiàn)可能暫居上風(fēng),它們絕不會(huì)聯(lián)合起來(lái)推出一個(gè)敵手和真正的天才競(jìng)爭(zhēng);相反,它們遲早總要對(duì)自然和正當(dāng)感受的力量投降。因此,雖則一個(gè)文明國(guó)家在哲學(xué)家中作孰優(yōu)孰劣的選擇時(shí)選錯(cuò)的情況屢見(jiàn)不鮮,在喜愛(ài)某一篇膾炙人口的史詩(shī)或某一個(gè)悲劇作家之類(lèi)的問(wèn)題上發(fā)生長(zhǎng)時(shí)期的錯(cuò)誤則是從來(lái)沒(méi)有的事。
到此我們已經(jīng)盡力給趣味確定一個(gè)標(biāo)準(zhǔn),借以協(xié)調(diào)人類(lèi)歧異百出的反應(yīng)了;但是還有兩個(gè)差異的來(lái)源,雖說(shuō)不能完全抹殺美丑之間的界限,卻可以影響我們褒貶的程度,使之有所不同。一個(gè)是個(gè)人氣質(zhì)的不同;另一個(gè)是當(dāng)代和本國(guó)的習(xí)俗與看法。趣味的普遍原則是人性皆同的;如果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判斷,一般總可以在鑒別力的缺陷和敗壞里找到根源,產(chǎn)生的原因可能是偏見(jiàn),或缺乏訓(xùn)練,或不夠敏感;最后終歸還可以舉出正當(dāng)理由肯定一種趣味,否定另一種趣味。但如果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外部環(huán)境都截然不同,而雙方又都沒(méi)有毛病,因此沒(méi)有抑此揚(yáng)彼的根據(jù);在這種情況下,一定程度的看法不同就無(wú)法避免,硬要找一種共同標(biāo)準(zhǔn)來(lái)協(xié)調(diào)相反的感受是不會(huì)有結(jié)果的。
情緒旺盛的青年比較容易受到戀慕和柔情等描寫(xiě)的感染;年齡老大的人則比較喜愛(ài)有關(guān)持身處世和克制情欲的至理名言。二十歲的人可能最?lèi)?ài)奧維德;四十歲可能喜歡賀拉斯,到五十歲多半就是塔西佗了。遇到這種情況,一定要擺脫我們自己的天然傾向以求“進(jìn)入”他人的感受,只能是徒費(fèi)心力。因?yàn)檫x擇喜愛(ài)的作家和選擇朋友是一個(gè)道理,性格和脾氣必須相符。歡笑或激情,感受或思考,這些因素不管哪個(gè)在我們的氣質(zhì)中占首要地位,都會(huì)使我們和與我們最相像的作家起一種特殊的共鳴。
甲喜歡崇高,乙喜歡柔情,丙喜歡戲謔。丁對(duì)缺陷特別警覺(jué),力求打磨光凈,毫無(wú)瑕疵。戊則對(duì)佳妙之處較更熱心,為了一個(gè)雄偉或動(dòng)人的形象可以寬恕二十處荒謬的“敗筆”。己的耳朵只能聽(tīng)進(jìn)簡(jiǎn)明洗練的文句;庚卻偏嗜華美繽紛、韻調(diào)鏗鏘的辭藻。辛主張樸實(shí),壬要求雕飾。喜劇、悲劇、諷刺詩(shī)、頌詩(shī)各有其擁護(hù)者,人人都認(rèn)為自己所偏嗜的體裁高于其他體裁。顯然,就一個(gè)批評(píng)家而言,只稱(chēng)許一個(gè)體裁或一種風(fēng)格,盲目貶斥其他一切是不對(duì)的;但對(duì)明明適合我們的性格和氣質(zhì)的作品,硬要不感到有所偏好也是幾乎不可能的事。這種偏好是無(wú)害的,難免的;按理說(shuō)也毋需紛爭(zhēng),因?yàn)楦緵](méi)有解決此種紛爭(zhēng)的共同標(biāo)準(zhǔn)。
同樣理由,我們?cè)陂喿x當(dāng)中總是更喜愛(ài)那些類(lèi)似我們時(shí)代和國(guó)家的描寫(xiě)和人物,對(duì)體現(xiàn)不同風(fēng)俗的描寫(xiě)和人物則比較冷淡。我們總要費(fèi)一番氣力才能接受“淳古之俗”,才能對(duì)公主自己去溪邊打水,英雄和國(guó)王自己烹調(diào)食物不感覺(jué)別扭。我們可以籠統(tǒng)地承認(rèn)描寫(xiě)這種風(fēng)俗不應(yīng)歸咎于作家,也不該算是作品的缺陷,但我們讀了確實(shí)不會(huì)深深感動(dòng)。唯其如此,喜劇從一個(gè)時(shí)代或國(guó)家移植到另一個(gè)時(shí)代或國(guó)家,才那樣困難。法國(guó)人或英國(guó)人不會(huì)欣賞臺(tái)倫斯的《安德羅斯的婦人》或馬吉阿維利的《克麗蒂亞》;因?yàn)樵谀莾善獎(jiǎng)”纠铮鳛槿珓£P(guān)鍵的女主人公連一次也不對(duì)觀眾露面,總是躲在幕后——而這樣正符合古代希臘人和現(xiàn)代意大利人的矜持脾氣。有學(xué)識(shí)肯思考的人對(duì)這種特別的風(fēng)俗可能毫不介意;但是顯然不能要求普通觀眾也全把他們習(xí)慣的想法和感情丟開(kāi),欣賞像這樣與他們自己毫無(wú)共同之點(diǎn)的場(chǎng)面。
寫(xiě)到這里我又想起一點(diǎn),可能對(duì)盡人皆知的今古學(xué)術(shù)之爭(zhēng)有所幫助。因?yàn)樵谀菆?chǎng)論爭(zhēng)里,一方面總是用時(shí)代習(xí)俗來(lái)辯解古人作品里一切荒謬難通的地方;另一方面則總不肯接受這種辯解,或者認(rèn)為接受了也只能寬恕作家,不能寬恕作品。據(jù)我看,論爭(zhēng)雙方常常沒(méi)有把正確界線劃定下來(lái)。凡是所描寫(xiě)的習(xí)俗雖然古怪卻無(wú)害處(如上文所舉的例子),那么肯定應(yīng)該容許;對(duì)這類(lèi)描寫(xiě)也表示震驚嫌厭只能證明鑒賞者自已的“敏感”和“高雅”分文不值。假使人類(lèi)對(duì)風(fēng)俗習(xí)慣的演化全不考慮,只肯接受符合當(dāng)前風(fēng)氣所趨的作品,詩(shī)人“比黃銅更經(jīng)久的紀(jì)念碑”就早會(huì)和破磚爛瓦一樣地坍倒了。難道因?yàn)槲覀兊淖嫦壬弦掠锌U領(lǐng),裙子有鯨骨,就把他們的畫(huà)像也都當(dāng)廢物拋棄嗎?但凡是遇到道德和體面的觀念也隨世遷移,描寫(xiě)邪惡的習(xí)俗而不予以正當(dāng)?shù)淖l責(zé)和申斥,這就得承認(rèn)是損害了詩(shī)篇,應(yīng)當(dāng)算作真正的丑。我不可能,也不應(yīng)該,使自己進(jìn)入這種感受;不管我怎樣考慮時(shí)代習(xí)俗而原諒詩(shī)人,要我欣賞他的詩(shī)作卻絕辦不到。某些古代詩(shī)人(有時(shí)連荷馬和希臘悲劇作家也是如此)刻畫(huà)的性格慘酷無(wú)理到駭人的程度,這不能說(shuō)不大大降低了他們杰作的價(jià)值,在這點(diǎn)上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現(xiàn)代作家更為優(yōu)長(zhǎng)。我們不會(huì)關(guān)心像那樣粗魯野蠻的英雄的命運(yùn)和感情;我們不愿意看到善惡之間的界限被蹂躪得一塌糊涂。不管我們?cè)鯓訉捤∽髡叩钠?jiàn),也絕不可能真正進(jìn)入他們的感受,或真正喜愛(ài)我們明明覺(jué)得是應(yīng)受指責(zé)的人物。
應(yīng)該看到,道德原則和理論主張完全不同。理論主張總在經(jīng)歷一個(gè)不斷流動(dòng)變革的過(guò)程,兒子信仰的體系和父親就會(huì)兩樣。甚至只就一個(gè)人說(shuō)來(lái),能夠自少至老恒久不變的情況也是絕無(wú)僅有。但不管何時(shí)何地的文藝作品中如果發(fā)現(xiàn)這種持論的錯(cuò)誤,對(duì)作品價(jià)值總不會(huì)發(fā)生多大影響;我們只需把腦筋和想象略作調(diào)整,就可以“進(jìn)入”當(dāng)時(shí)所信奉的那些論點(diǎn),然后欣賞從中產(chǎn)生的感受和結(jié)論。但要我們改變對(duì)人類(lèi)行為的判斷,脫離我們所長(zhǎng)久習(xí)慣的標(biāo)準(zhǔn),硬擠出一套全然不同的褒貶或愛(ài)憎,則必須付出九牛二虎的氣力。如果一個(gè)人深信自己判斷所依據(jù)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完全正確,那么他就有正當(dāng)理由對(duì)這種標(biāo)準(zhǔn)謹(jǐn)加護(hù)持,拒絕為了照顧任何作家的“情面”而歪曲自己的內(nèi)心感受。
在一切持論錯(cuò)誤當(dāng)中,有關(guān)宗教的錯(cuò)誤,如果發(fā)生在天才作品里,最不宜于苛求;事實(shí)上,我們也從不認(rèn)為應(yīng)該根據(jù)任何民族甚至任何個(gè)人所信奉的神學(xué)道理或精或陋來(lái)判斷他們的文明或智慧。原因是指導(dǎo)我們?nèi)粘I畹囊?jiàn)識(shí)在宗教問(wèn)題上無(wú)法施展,因?yàn)樽诮虤v來(lái)被認(rèn)為是完全超乎人類(lèi)理性之上的。所以一切企圖公正估價(jià)古代詩(shī)歌的批評(píng)家必須把那套神道設(shè)教的悠謬之談置之不論;對(duì)我們自己的后代,我們也得要求同樣的寬容。不管什么樣的宗教信條都不該歸咎于詩(shī)人——只要僅僅是信條,而不是把他弄得神魂顛倒以至達(dá)到頑固或迷信的地步。一旦達(dá)到那種地步,道德觀念就會(huì)陷入一團(tuán)漆黑,善惡的天然界限也就隨之改變。因此,根據(jù)上述原則,這就應(yīng)該算是不可磨滅的缺點(diǎn),援引當(dāng)代的偏見(jiàn)和錯(cuò)誤看法并不足以為這種缺點(diǎn)作辯護(hù)。
羅馬天主教的一條中心教義就是叫人痛恨一切其他信仰,把異教徒、回教徒和旁門(mén)左道都說(shuō)成是神怒天罰的對(duì)象。這種看法按其實(shí)質(zhì)自然是應(yīng)當(dāng)譴責(zé)的,但是那個(gè)宗教團(tuán)體里的虔信者卻把它視為美德,并且當(dāng)作一種神圣的英雄主義寫(xiě)進(jìn)他們的悲劇和史詩(shī)里。這種頑固態(tài)度損害了兩篇本來(lái)十分美好的法國(guó)悲劇:《波利約克特》和《阿塔利》;它們都大肆渲染對(duì)某些特殊信仰方式的瘋狂熱情,并且把它作為主人公性格的突出一面。當(dāng)器宇莊嚴(yán)的若阿發(fā)現(xiàn)若薩貝和巴里祭司馬當(dāng)交談的時(shí)候,他這樣大聲咆哮:“怎么?大衛(wèi)的女兒竟然和這個(gè)叛徒談話嗎?你不怕這些神圣的墻垣會(huì)崩倒把你倆都?jí)核绬幔磕悴慌麓蟮貢?huì)裂開(kāi)噴吐火焰把你倆都吞下去嗎?他是抱著什么目的?為什么這個(gè)上帝的敵人要來(lái)到這里,用他的丑形惡貌毒化我們呼吸的空氣?”像這類(lèi)的感情可以在巴黎舞臺(tái)上博得熱烈喝彩,但是對(duì)倫敦的觀眾說(shuō)來(lái),其效果和聽(tīng)到阿喀琉斯罵阿伽門(mén)儂“面目像狗,膽量像鹿”,以及丘必特恐嚇朱諾,再不閉嘴就要老實(shí)揍她一頓,是一樣的叫人皺眉搖頭。
宗教信條一旦“上升”為迷信,不管什么與宗教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情感都要加以附會(huì)——這也是文藝作品的缺陷。固然本國(guó)習(xí)俗可能特別著重宗教禮節(jié)和儀式,以至生活各部門(mén)都不免受到它的壓制,但詩(shī)人卻不能以此為自己辯解。佩脫拉克把情人蘿拉比作耶穌基督總歸是可笑的;薄伽丘——那討人喜歡的放浪作家——竟一本正經(jīng)地感謝“威力無(wú)邊的上帝”和其他貴婦人保衛(wèi)自己免受仇敵陷害,也是同樣荒唐。
后記
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是英國(guó)著名的哲學(xué)家、歷史家和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他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論》(1739—1740),《道德與政治論文集》(1741—1742),《人類(lèi)理智硏究》(1748),及《英國(guó)史》(1754—1761)等。本文是從《道德與政治論文集》第一卷(1875年倫敦兩卷本)里選錄出來(lái)的。
休謨的美學(xué)思想不過(guò)是他整個(gè)哲學(xué)體系的一個(gè)側(cè)面或支流。由于他的哲學(xué)體系是主觀唯心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因此他堅(jiān)持所謂“美不是事物的內(nèi)在屬性”這一論點(diǎn),并且在這篇文章里再三致意。但他也看到徹頭徹尾的相對(duì)論:“情人眼里出西施”或本文所援引的“趣味問(wèn)題無(wú)需爭(zhēng)辯”終竟站不住腳;因?yàn)樾葜冎雷鹬亟?jīng)驗(yàn),他看到人類(lèi)的美學(xué)感受經(jīng)驗(yàn)有極大的普遍性,甚至“比哲學(xué)或科學(xué)問(wèn)題更容易得到定論”,所以他又主張有一個(gè)絕對(duì)客觀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為了調(diào)和這個(gè)矛盾,他提出如下的看法:美屬于感受范疇,但事物的某些屬性天然可以喚起那種感受。這種天然因果關(guān)系是受一定規(guī)律控制,可以用一定規(guī)律表述的。所有歧異都發(fā)源于感受過(guò)程中的偏差,因而歪曲了該規(guī)律在我們意識(shí)中的正確反映。對(duì)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他只作出兩點(diǎn)保留;即個(gè)人氣質(zhì)和社會(huì)習(xí)俗的不同;但對(duì)它們的適用范圍,也劃出了嚴(yán)格界限。從消極方面看來(lái),休謨對(duì)各種偏差如反歷史主義、宗教熱狂、忽視對(duì)象等等的抨擊還有一定借鑒意義。
應(yīng)該指出:本文主要是針對(duì)文學(xué)作品而寫(xiě)的,因?yàn)樾葜儗?duì)造型藝術(shù)并不在行。《休謨傳》的作者勃吞曾說(shuō)過(guò):“就我記憶所及,在他一生行事及書(shū)信往來(lái)中從未透露過(guò)任何真正愛(ài)好某一幅畫(huà)或某一座雕像的痕跡”(第二卷134頁(yè))。這方面知識(shí)的欠缺無(wú)疑也給文章帶來(lái)了較大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