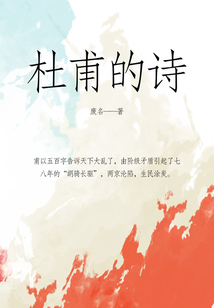
杜甫的詩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意義
我們分析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這首詩,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意義太大了,是劃時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杰作。詩寫的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十月——十一月的事情,其時這個統(tǒng)治主正在“幸華清宮”,同楊貴妃一塊兒。杜甫因為他的家寄住在奉先,他從長安動身到奉先去,第二天清晨經(jīng)過驪山——華清宮所在地,受了非常大的刺激,真是悲憤填胸,大約就在到家后寫了這一首《詠懷》。安祿山的亂本來就在這個十一月里發(fā)生了。這是一個大變亂,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對人民說也是一個大災(zāi)難。杜甫的這五百個字,反映了這個時代。
從前有人說:“文之至者,但見精神,不見語言。此五百字,真懇切至,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處見有語言!”這話對這首詩是能有所認(rèn)識的。杜甫寫這首詩時的思想感情真是太急迫了,要說的話太多了。向來以這首詩與《北征》相提并論,比起《北征》來,《自京赴奉先詠懷》字?jǐn)?shù)要少些,然而意思確是顯得更多更多,思想感情確是顯得更重更重。就詩的語言說,這首詩還有一般舊日作詩的缺陷,就是表現(xiàn)一件事情不是用確切的活的詞匯,而是用典故來代,從故紙堆中找僻生的字來用,如“蚩尤塞寒空”以“蚩尤”代旌旗,“樂動殷膠葛”——又作“殷嶱嵑”或什么,反正都是失掉作用的詞匯。這個現(xiàn)象《北征》里便沒有。《北征》里象“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的句子,不能算是用了死字眼,是描寫得很生動的,因為“天吳”“紫鳳”同是具體事物的名字。不過《赴奉先詠懷》里的典故和僻字,就是說當(dāng)時已經(jīng)失去作用的詞匯,還是極少數(shù)的,而且杜甫用來也同無病呻吟的人作詩慣用死典故死字眼不同,慣用死典故死字眼是掩飾自己沒有意義,是堆砌,什么也沒有表現(xiàn),杜甫則是要表現(xiàn)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又確實(shí)不好表現(xiàn)。不好表現(xiàn)約有兩種原因,一種原因是舊日詩的體裁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上受了限制;一種原因是這件事情的性質(zhì),好比“蚩尤塞寒空”是描寫唐朝皇帝同了妃子住在山上取樂,要許多衛(wèi)兵守護(hù)著,遠(yuǎn)望山上盡是旗子,杜甫當(dāng)然不能當(dāng)作好看的風(fēng)景來寫,表現(xiàn)起來便有些困難。“樂動殷膠葛”也是一樣,寫時是厭惡它,但怎么寫這個音樂的聲音呢?確有困難。杜甫只是告訴我們有這些事情罷了,我們讀著知道這些事情罷了。我們現(xiàn)在讀古人的詩,在語言方面不要給典故和僻字嚇唬住了,或者受了它的迷惑,以為它令我們不懂便是它的奧妙。其實(shí)真正的好的語言決不是叫人不懂的,而是叫人格外懂的。好比這幾句:“況聞內(nèi)金盤,盡在衛(wèi)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zhì)。”借漢朝皇帝內(nèi)戚來指唐代姓楊的,并把楊妃都描寫出來了,是以極少的語言寫不少的事情,正是舊日詩的長處。在這里用的典故——“衛(wèi)霍”,同比喻一樣,同例證一樣,是修辭所容許的,是應(yīng)該用的。舊日詩的表現(xiàn)作用,有時有所短,而更多的場合是有其所長。到了“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則充分發(fā)揮了詩的長處,煖客四句連忙接到“朱門酒肉臭”,又連忙接到“路有凍死骨”,意思明白不用說,而力量大極了,把作者的思想感情一下子傳給了讀者,在散文里便沒有法子來得這么快,這是韻文勝過散文的地方。而這里并沒有典故,并沒有僻字。聯(lián)到自己家庭在奉先時,這樣寫:“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fēng)雪!”都是老杜驚人的語言,把苦難的日子寫得非常有形象,仿佛天下的人各自有其老幼男女,各自在風(fēng)雪之中,一家人聚在一塊兒也無非是擠凍挨餓而已。所以接著便是:“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好的語言好的詩是用不著典故和僻字的。典故和僻字在舊日詩里有時確是不能不依賴它,好象在某種情況之下走路不能不拄棍子,我們千萬不要為它所迷惑,我們要把它當(dāng)作普通話一樣用語法同詞匯來衡量,那么它的好丑便難逃我們的眼睛。我們在這里應(yīng)該首先交代這一層。
杜甫以五百字告訴天下大亂了,由階級矛盾引起了七八年的“胡騎長驅(qū)”,兩京淪陷,生民涂炭。而在《自京赴奉先詠懷》以前寫的詩里詩人已暴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剝削、荒淫、腐敗、自私、不顧人民的事實(shí),同時替人民作了記錄,支持封建唐朝唯一的兩件事——租和兵,人民是怎樣擔(dān)當(dāng)起來。這有有名的《兵車行》和《麗人行》。此外有一首《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篇幅雖較短,而是同屈原《離騷》同性質(zhì)的作品,也是杜甫的詠懷,也諷斥了唐明皇同楊貴妃,也罵了跟著皇帝的官,“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我們可以把這些詩同《自京赴奉先詠懷》聯(lián)系起來看。
杜甫個人在天寶十四年(這年他四十四歲)本來開始有了一個官職,初授河西尉,他沒有做,改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他做了,連忙又要不干的樣子。關(guān)于此事他有兩首詩,我們有一談之必要。一首是《官定后戲贈》,自己贈給自己;一首是《去矣行》。《官定后戲贈》云:“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圣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fēng)飚!”這說明杜甫同陶淵明一樣不肯“折腰”,但時代不同了,陶淵明的時代,一個貴族在鄉(xiāng)下住著,雖然窮一些,人家還要尊重他的門第,我們在陶詩里可以看出陶淵明窮而受到尊重的情形;唐朝是科舉時代,地主階級是一步步向上爬的,你沒有“衣錦”而“還鄉(xiāng)”是沒有人瞧得起的,所以杜甫曾訴苦:“鄉(xiāng)里兒童項領(lǐng)成,朝廷故舊禮數(shù)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lián)百結(jié)。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咸華兩縣諸子》)陶淵明是不至于這個樣子的。杜甫不肯“折腰”做河西尉,大可以賦“歸去來兮”了,然而“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fēng)飚!”這就是說陶淵明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實(shí)際上杜甫的家這時已無法安置在奉先(詳情我們雖然不知道),便是“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fēng)雪”的境況。他個人在長安“率府且逍遙”。說是“逍遙”而又覺得可恥,我們看他的《去矣行》:“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lán)田山!”他說“餐玉法”是說氣話,明天就要走罷了。所以他寫了《去矣行》之后接著就是《自京赴奉先詠懷》,這兩首詩合起來便等于杜甫寫了他自己的“歸去來兮辭”,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杜甫是很佩服陶淵明的,兩位詩人的思想感情常有矛盾也相同,而杜甫又曾批評陶淵明:“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dá)道!”(《遣興五首》之三)那么在杜甫看來什么叫做“道”呢?我們應(yīng)該重視《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杜甫的“道”的意義應(yīng)該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詩的“人民性”,就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精神。時代變化了,生活復(fù)雜了,杜甫的詩所表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主義乃超過他以前的任何詩人。而在杜甫以后的中國封建社會所產(chǎn)生的任何詩人——或者因為染了佛教道教的臭味,或者因為“官”氣重些不及杜甫的生活同人民接近,也都沒有杜甫的愛國愛人民的深厚感情、偉大詩篇。
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很明白的,《自京赴奉先詠懷》暴露而且控訴了統(tǒng)治者,國家的棟梁應(yīng)該沒有別的人而是交租稅服兵役的勞苦大眾,作者自己也屬于剝削階級。作者所沒有認(rèn)識清楚的是“皇帝”——詩里非常天真地叫作“圣人”,這到底是一個什么東西?這無非是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魔術(shù)名詞,支配了任何人的思想意識,作者認(rèn)為顛撲不破罷了。若檢查一下具體生活當(dāng)中的人,連詩人杜甫也可恥,因為同勞動人民比起來“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我們看這幾句詩:“圣人筐篚恩,實(shí)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這算是杜甫的哲學(xué),是“至理”,根據(jù)他的詩里所控訴的一件一件的事實(shí),這所謂“至理”,完全站不住腳,徒徒表示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事實(shí)的歪曲。事實(shí)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為什么在你的哲學(xué)里忽然又把這寒女家鞭撻出來的東西認(rèn)為是“圣人筐篚恩”呢?然而詩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他要求“至理”,他寶貴“此物”,他“實(shí)欲邦國活”,所以他的詩反映了真實(shí)的歷史,真實(shí)的歷史是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對立。從本篇看來,當(dāng)時農(nóng)民“失業(yè)”“遠(yuǎn)戍”,從《兵車行》看來,遠(yuǎn)戍而家里還是逃不了“縣官急索租”。在杜甫其余的詩里寫租稅寫兵役兩件事的太多太多,明明指出男子服兵役死了而女子還是要在家納稅的有:“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遣遇》)我們再舉個例子看剝削者方面,杜甫自己在夔州的時候雇了人種了稻田植了果林,當(dāng)然足以代表地主階級,而他在夜里寫詩,一首說“暫憶江東鲙,兼懷雪下船”,一首寫其聞見:“甲兵年數(shù)久,賦斂夜深歸。”(《夜二首》)詩人只是有良心聽見農(nóng)民半夜里納賦回來把事情記在自己的詩里,過的卻明明是有特權(quán)的生活。所以邦國之得以茍活,完全靠勞苦大眾支持,這是封建中國的實(shí)質(zhì)。杜甫說他“默思失業(yè)徒,因念遠(yuǎn)戍卒”,他并不是在這篇《詠懷》里寫兩句詩就算了,他平日真是“思”,真是“念”,他的《前出塞》《后出塞》都是在“思”在“念”之下給我們留下了國家真正的主人平凡而偉大的勞動人民的形象。他在《夏夜嘆》里還這樣地思念著:“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zhí)熱互相望!”這是想起荷戈之士天熱沒有法子洗澡。我們真要學(xué)習(xí)杜甫,看杜甫是如何地愛勞動人民,愛兵!除了“失業(yè)徒”“遠(yuǎn)戍卒”而外,我們把《自京赴奉先詠懷》里面的名字再檢查一下,什么“堯、舜”,什么“巢、由”,什么“當(dāng)今廊廟具”,什么“多士”,什么“仁者”,都是好名詞,代表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tǒng)哲學(xué),而歷史證明這是地主階級自欺欺人。倒是“圣人”同了“神仙”在“路有凍死骨”的日子在音樂當(dāng)中在山上溫泉里“浴”或者“賜浴”,有其人,有其事。然而我們?nèi)绻f詩人如果當(dāng)?shù)溃ㄋ?dāng)然不會當(dāng)?shù)溃⑷绾文軡?jì)于事,“竊比稷與契”,那又是上了哲學(xué)的當(dāng)。我們只要讀一讀杜甫向“圣人”獻(xiàn)的《三大禮賦》,便知道那與國計民生是一點(diǎn)也不相干的。我們再讀一讀他后來寫的《洗兵馬》,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頌詩,除了最后幾句勸農(nóng)的話寫出國家的實(shí)際責(zé)任歸根結(jié)蒂落在打完仗平了寇(其實(shí)寇還沒有平)回來的農(nóng)民頭上而外,沒有一句話配得上叫做政治的內(nèi)容,什么“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什么“鶴駕通霄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簡直不象杜甫的詩了。原因非常簡單,歷史上中國的封建統(tǒng)治,幾個最初建國的皇帝,因為從民間起來,受了階級斗爭的教訓(xùn),現(xiàn)在知道要緩和斗爭,稍稍滿足農(nóng)民的要求,尚談得上一些政治措施,至于他們的子孫,自然便一個個地壞下去,暴露剝削階級的本質(zhì),——這是不可能有例外的。這個政權(quán)之下的詩人,說什么“竊比稷與契”,同“生逢堯舜君”一樣是腐儒的話。
我們對《自京赴奉先詠懷》起首一段的話還應(yīng)該作必要的分析。詩人杜甫同時確是中國封建社會一個極其素樸的哲學(xué)家。他生于宋代理學(xué)家之前,所以他是儒家而不談玄學(xué),他只說他“竊比稷與契”。他呼吸了魏晉老莊哲學(xué)派的空氣,所以他明明受了孔孟——尤其是孟軻的影響很深,而他又毫無拘束地說著“孔丘盜跖俱塵埃”(《醉時歌》)的話,表現(xiàn)在《自京赴奉先詠懷》里便有這樣的莊周“齊物”的思想:“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輒擬偃溟渤?”可惜他常常有求人的事情,因為這些可恥的事也寫了一些“干謁”的詩,所以接著他說“獨(dú)恥事干謁”,并不是說自己沒有干謁,倒是說“恥”。他批評陶淵明“未必能達(dá)道”,而他“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jié)”的感情又確是很重的,在他后來的詩里表示過不只一次。臨死之年寫的《登舟將適漢陽》一詩里還說著“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jī)。”但從杜甫前前后后的詩里證明他決無意于做“蕭灑送日月”的名士一派,這一派人當(dāng)中最豪放、最富有感情的象后來詩人辛棄疾也還是“閑飲酒,醉吟詩,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說得好聽“管竹管山管水”,其實(shí)是地主。杜甫當(dāng)然過了這種地主生活,他在夔州的生活便是很明顯的,然而他總是說老實(shí)話的時候多,他對被剝削者說“日驚未餐,貌赤愧相對!”(《信行遠(yuǎn)修水筒》)所以“取笑同學(xué)翁,浩歌彌激烈”,應(yīng)該翻轉(zhuǎn)來說是他笑別人,別人不配笑他。杜甫一生的生活,一生寫的詩,告訴我們他的思想是真實(shí)的,他沒有說一句門面話,這是杜甫最不可磨滅的地方。其所以能如此,最主要之點(diǎn)還在于他的生活接近人民,他真懂得人民的痛苦。“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這四句,便是杜甫的寫照。我們真應(yīng)該愛他,愛他這四句話,在這里不能有一點(diǎn)夸大,而是不夸大的最偉大詩人呵!“此志常覬豁”,所謂“志”便是“詩言志”的志,他的詩,便是“窮年憂黎元”的詩。統(tǒng)觀杜集,用他自己的話,“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那是關(guān)于表現(xiàn)方法,用他自己的話又正是“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這是寫詩的精神。陶淵明自白其“酣觴賦詩,以樂其志”,杜甫的“豁”字便等于陶淵明的“樂”字。杜甫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偉大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詩人。
我們還應(yīng)該簡單然而扼要地把唐代以前幾個偉大的詩人——就他們的詩所反映的社會現(xiàn)實(shí)這一個主要問題,拿來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作一個比較。一句話,杜甫以前的詩人的詩里所反映的矛盾不超過詩人本階級內(nèi)部的矛盾,杜甫的詩,如我們上面所分析,則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個階級的對立。我們先看屈原,屈原感情熱烈,想象豐富,語言風(fēng)格更特別有創(chuàng)造性,若問他當(dāng)時為什么寫《離騷》,應(yīng)該就是這幾句話的回答:“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邃遠(yuǎn)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fā)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當(dāng)時的“賢”當(dāng)然是立于人民利益方面的,然而“溷濁”是統(tǒng)治階級的溷濁,“賢”同“濁”是一個階級里面的事。曹植更不用說,他的“拔劍捎羅網(wǎng)”的思想感情,主要是因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來的。阮籍同陶淵明很有相象的地方,陶淵明耕田不用說,阮籍也很想“耕”,所以他的《詠懷》說:“愿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不過阮籍當(dāng)時所處的階級內(nèi)部矛盾非常利害,他很容易有性命的危險,他只能靠“醉”來解決。他的詩所表現(xiàn)的感情極強(qiáng),語言美麗:“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這就是表示他妥協(xié),他不怕“曲”,因為龍也是曲。這當(dāng)然是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事情。陶淵明耕田也只是解決他個人思想矛盾(也就是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的手段,在陶詩《飲酒》篇里有一首寫一個農(nóng)民勸他“襤縷茅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愿君汨〔汩〕其泥”,很明白,勞動人民知道隱士的身分了。我們再看鮑照的這一首《擬古》:“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澗陰。朔風(fēng)傷我肌,號鳥驚思心。歲暮井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送函谷,獸藁輸上林。河渭冰未開,關(guān)隴雪正深。笞擊官有罰,呵辱吏見侵。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前面一十二句不很象杜甫的先聲嗎?然而“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是鮑詩的主題思想,與杜詩有著質(zhì)的差異。杜甫的劃時代的《自京赴奉先詠懷》,可以當(dāng)作還沒有階級覺悟的老實(shí)人的一篇反省,里面反映了兩個階級,控訴以皇帝為首的本階級即地主階級,同情被剝削被壓迫的農(nóng)民階級。
最后我們附談一件有趣的事,要象我們現(xiàn)代的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就必須愛憎分明,把統(tǒng)治者與人民的界線劃得清清楚楚,屈原、阮籍、陶潛等都是古人,而且是貴族,當(dāng)然不能夠。獨(dú)有杜甫,他的恨眉有時橫起來了,同時就因為哀我黎民。我們抄他這首《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cè)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勞勞。下愍百鳥在羅網(wǎng),黃雀最小猶難逃。愿分竹實(shí)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這最后兩句,“愿分竹實(shí)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不很象現(xiàn)代魯迅的口聲嗎?杜甫是偉大的,可以說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他是第一個把人民和統(tǒng)治者分開,愛憎分明的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