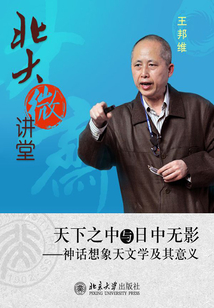
北大微講堂·天下之中與日中無影:神話想象天文學及其意義
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首先是要謝謝陳老師的介紹,剛才陳老師說跟我有三個相同點,其實還有第四點:我記得陳老師好像是1987年博士畢業的,我也是1987年博士畢業。當時北大的博士研究生很少,大概只有幾十個吧,所以應該說我跟陳老師有四個共同點。過去科舉時代,同一年考上的就稱作“同年”。但我年紀比陳老師大,所以陳老師得叫我一聲“年兄”,而我得稱呼陳老師一聲“年弟”。
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是跟我糾纏了十多二十年的一個問題,天下之中與日中無影。長期以來我逐步通過讀書、通過旅行,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思考,最終,這個問題基本已得到解決。今天,就向大家報告一下,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心得,看到這個題目,大家可能會覺得怪:怎么會扯那么多東西進來,什么神話、想象、天文學、天下之中與日中無影?這里,我先簡單說明。第一,所謂“天下之中”。我們知道,古代的中國人通常認為,我們中國是處在世界的中心,我們中國是中央之國,英文叫Central country under the heaven。這個中央之國,是中國人的一個想象,當然那是古代的中國人,當時對整個世界的了解還很少,所以不奇怪。什么叫“日中無影”呢?大家知道,太陽光照在地上,物體在地面會投出其影子,這個影子從太陽升起到落下,是不一樣的,有長有短;更重要的是,假設這物體長期因定不動,其日照投影呈象在每天的不同時刻、一年的不同時間,也是有長有短,不一樣的。進一步而言,當天上的太陽日光正垂直于地面時,人站在太陽之下是沒有影子的,或者豎一根桿子同樣是沒有影子的。
那么,“日中無影”怎么會跟“天下之中”連到一塊呢?這正是我下面要講的內容。在開始我下面的報告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紹三本書:
第一本書是《周禮》,這本書大家可能熟悉一點,尤其是文科的同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同學。《周禮》是儒家的經典,屬于儒家的十三經之一,也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文獻,是構成中國文化最基礎的一些文獻之一。它是一本講古代禮制的著作。上一次的才齋講堂,閻步克嚴老師講的好像是官制。最早的官制,一部分就跟《周禮》有關系。
第二本書是《山海經》,這本書大家大概也知道。《山海經》[1]是一部類似于神話的書,但它其實不完全是神話。從類型上講,它跟《周禮》完全不一樣。它講山、講海,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先民對周圍世界的一種神話性的想象。我們現在知道的很多神話,就是從這里來的,像夸父追日、精衛填海,還有刑天舞干戚。這是一本很奇怪的書,到現在為止,大家都說這個。古代的評價是“恢怪不經”。司馬遷就評價過這本書,他說他是看不懂的。司馬遷是2000多年前的人,他都說看不懂。我們現在有不少學者研究這本書,研究者們覺得,這本書保留了中國最古老的一些神話和傳說。這已經成為一門學問。這是第二本書。
注釋
[1]唐人杜佑(著《通典》者)認為“《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
第三本書是《南海寄歸內法傳》。這本書大家可能不大知道。唐朝初年,也就是唐高宗的時代,中國有一個和尚叫義凈,“義”是“意義”的“義”,“凈”是“干凈”的“凈”。大家都知道唐朝初年到印度去取經的玄奘和尚,也是《西游記》中的玄奘。但其實義凈和尚也不比玄奘差,他在玄奘去了印度40年后,也去了印度。他跟玄奘不一樣的是,他是坐船,從海路去的。他從廣州出發,坐船首先經過現在的中南半島,或者叫印度支那半島,然后經過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進而取道馬六甲海峽,到達東印度。然后他在印度學習了大概十多年。他從印度回來的時候,船就停留在蘇門答臘島。當時蘇門答臘島上有一個很有名的國家,叫室利佛逝國,這在中國史書里有記載。室利佛逝國就在蘇門答臘東部,大概在現在蘇門答臘東部一個最大的城市,叫巨港的位置。巨港是蘇門答臘島最大的一個城市,印尼人叫Palambang,中國人管它叫做巨港。義凈在室利佛逝國停留了六年,在停留期間,他寫了這本書。因為古代中國把整個南海一帶,也就是現在的東南亞一帶都叫做南海。義凈把書寫好之后,還請人把它送回國,交給當時已經做了皇帝的武則天,所以書名就叫《南海寄歸內法傳》。“內法”就是指佛教。他在這本書里,把他當時到印度取經,求法時所見到的東南亞一帶及印度一帶的很多情況做了很詳細的記載,主要與佛教有關,也有關于當地社會生活、地理交通、物產等等。這本書一共有四萬多字,其實是非常有名的一本書,不過在國內知道的人反倒不是很多。但它在西方所謂的東方學界很早就有名。1896年,牛津大學就出版過這本書的英譯本,是日本一位非常著名的學者高楠順次郎(1866—1945)翻譯的。這位學者憑借這本書翻譯獲得了他的博士學位,后來成為東京大學的第一任梵文教授,是日本現代印度學、梵文學、印度哲學學科的創始人。
這是我介紹的三本書,我分別結合這三本書來談這個“天下之中”和“日中無影”的問題。
下面講的第一本書《周禮》。《周禮》一共分六篇,其中一篇的篇名是“地官”。《地官》里有一章叫《大司徒》,大司徒里邊有這么一句話“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大家注意這個“景”字,古漢語“景”跟“影”是一個字,所以“正日景”實際上就是“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冷;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前面說了,用這個土圭,豎立一個石表,通過觀察太陽的影子,影的長短,尤其是夏至日的日影,來確定這個地中的位置。我們中國的大部分的位置,是在北回歸線以北,最南部在北回歸線以南,就是廣州一帶,也都是在北回歸線附近了,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都在北半球,所以太陽的影子是冬天最長,夏天最短,它是從南邊照過來的(我不知道我們同學的學科背景,但應該是學理科的和學文科的都有吧?)。但是這里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太陽的影子在一年的變化。究竟變化在哪?我們知道,在古代,太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測標志,而且可以說人類的天文觀測就是從觀測太陽開始的,然后才是月亮,再然后是行星。《周禮》從理論上來講,它是周公當時寫下來的,但實際上不是;而且它記載的是周公制立的制度,但實際上也不完全是。這個著作大概是在戰國年間形成的,它就保存了很多戰國以前的資料,雖然不一定全部是歷史事實,但有相當一部分是歷史事實。那就是說,“土圭之法”是有一定依據的。根據“土圭之法”的描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當太陽的影子有一尺五寸長的時候,那這個地方的位置就是地中。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因為《周禮》大致于戰國時期,所以后來就有很多對它進行來做解釋,也就是漢儒的解釋。漢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學者叫鄭玄,他引用了另外一名學者的解釋,這位學者也挺有名,叫鄭眾。鄭眾就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他說把桿或者表成直角豎起來,下面橫著的叫圭,豎著的叫表,他說“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適當與土圭等,謂之地中。”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就是地中。“今穎川陽城地為然。”穎川陽城在什么地方?就在今天河南洛陽附近的登封市,古代的登封縣,現在叫登封市,登封這個名字還是武則天取的。登封市有一個鎮,古代叫“陽城”,就是今天的“告成”,穎川陽城就在這個地方。《周禮注疏》是唐朝相當有名的學者賈公彥給“周禮”做的注疏。《周禮注疏》卷十言:“鄭司農云:穎川陽城地為然者,穎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這里說的這個地方就是現在洛陽附近登封市的告成鎮。周公當年為了建洛陽城,就用豎表來測太陽的影子。這很重要,因為太陽影子的作用一個是用以測定時間,還有一個是用以測定方位,方位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根據歷史的傳說和記載,洛陽城就是周公興建的。而且根據文獻記載,唐朝時這里有一個周公的“度景之處”,就是他測量影子的地方,這是當時的說法。
那么什么叫“地中”呢?我們看清朝有一個很出名的學者孫詒,他在《周禮正義》中言道:“地中者,為四方九服之中也。《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他的意思是說“地中”就是天下的中心;“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是說要和周邊接近的話,沒有比這個中央更好的了,所以王者立于天下之中也。他說“禮也”。“禮”就是規矩。這是我們中國的規矩,中國的規矩就是王者要住在這個天下之中。
這是我剛才講的影子、天下之中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接下來我要講第二本書,就是《山海經》。
首先我要說明,《山海經》是一部內容很龐雜的書,我只講《山海經》中間和本講有關的,即——“都廣之野”與“建木”、“日中無影”與“天下之中”。
《山海經》有很多經,其中有《海經》、《山經》,又各自分為內經和外經,其中有一部經叫《海內經》。我們要注意一點,我們現在講的“中華民族”實際上是一個具多元性、混合性的民族。這部《山海經》從文化系統面言,其實跟《周禮》是不在一個系統上的,它講的都是很奇怪的東西。例如《海內經》里講道“西南海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就是說西南海及黑水之間有個“都廣之野”;其還講道“后稷葬焉”,這個后稷是周人的尸骨,就是我們說的夏商的尸骨。“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其又講:“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焉。……有九丘,以水繞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即之丘。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嗥爰過,黃帝所為。”那個地方有樹木叫若木,還有陶唐之丘等九丘。還有一種木——“建木”,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種木。它說這種木是“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仭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皥爰過,黃帝所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