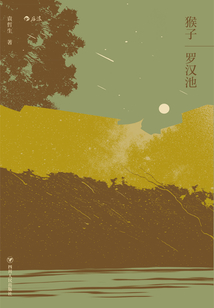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代序:時程的反證
文/童偉格
我認識小說家袁哲生,是他辭世前四年的事。那時,他剛到男性時尚雜志《FHM》擔任主編,而我,則是一名還畢不了業的大學生。他找我去,加入供稿的寫手群。我們偶爾見面,見了面,就一起灰撲撲地抽悶煙,很少說話,更少認真討論所謂“文學”。主要因為這事,有點像是各自心中隱私,令人害羞,不好光天化日談,除非,是用自嘲的語氣講。他交代工作指示時,也總是清爽扼要,不耍弄玄虛,不太夾帶個人感想,大致,就是從我已繳的稿件中,圈出具體段落,要我改得更明了,或刪得再更簡短些。
這類指示聽來容易,做起來才知道艱難。因當時,我工作內容之一,是去圖書館翻報紙社會版,從中擇取舊聞,重新敘事,集組成稿件。在絕不容許虛構的情況下,改寫與刪修,就有點像是在局限格框里,不斷琢磨素材的工匠細活了:你必須用字經濟,但行文卻仍直白口語地,將一件事的來龍去脈妥善描述,且描述自身,還必須煥發一種洞穿事理荒謬性的幽默感。更重要的是,面對種種世情,敘事者你必須保持絕對冷距,接近聲色不動。
我明白袁哲生的認真,是在他的標準并無二致:在技藝層次,他怎么要求自己的創作,就怎么要求寫手稿件。不,說來,他對待自己,當然還是比對待寫手要更嚴苛許多。寫手在闖不過關卡時,盡可以軟爛耍廢,說主編我盡力了,好不好就這樣刊出吧,小說家則沒得跟自己推托。且殘酷的總是,也不是他自覺盡力了,小說就能趨近理想了。
也是在那時,我讀完所有他已出版的小說集。我理解且敬佩,因這必定是十分費力的書寫實踐。因袁哲生的美學原則,是用白描修辭,留白不可言說的,這使他的敘事,總有一種一再打磨敘事的嚴謹質地。而這般鋒利的敘事,卻是為了重現一種敬遠:不可言說的,他依舊不會在小說里輕率表述,或僭越角色去發聲。這種自我節制,使他的小說,為讀者總體封存一種近觸存在本質的體感。我猜想他的書寫,像是一種指認,或體驗的原樣奉還,幫助我們,實歷我們必然常習,但卻始終失語的真確感知。一如所謂“孤獨”。
也于是,就技藝層次而言,一方面(一如這句我們熟悉的老話:在卡夫卡之前,我們不知道“孤獨”是什么),袁哲生就像所有優秀現代小說家,嘗試憑借個人語言勞動,孤自潛入存有的幽暗處,像一名最專誠的翻譯者,以小說,譯寫出午后雨點,盛夏蟬鳴,與一切景象,所共同親熟的本質性悲傷。使長久埋伏的,在小說里恍然兌實。另一方面,當這種純粹悲傷,漫漶小說里一切人事時,袁哲生總使日常細節,對我們而言再度陌異了:因為袁哲生,我們竟不可能確知,人世里,什么可以“不孤獨”。
閱讀袁哲生,因此意味著在親熟與陌異的感受間拉鋸。這種很具張力的矛盾,也體現在他對“小說”一事的倫理設想上:一方面,他鍛煉書寫技藝,磨成解析度極高的敘事能力;另一方面,如上述“敬遠”,或“自我節制”,他追求的理想文體,卻是一種必要藏起個人風格的,仿佛渾然天成的晶瑩介質,可用以絕無雜訊地擬像。這是說:這位卓然有成的小說家,事實上,將自己全心投入的藝業,與藝業中的自己,皆看待得十分遜退。
收錄于本書的五篇小說,原初,是在2003年時,分作兩部小說集出版:《雨》與《猴子》兩篇,收錄于《猴子》一書;《月娘》《羅漢池》與《貴妃觀音》等三篇,則收錄于《羅漢池》。很明確,依袁哲生的規劃,這是兩組小說系列連作,結構概念上,如同他在《秀才的手表》(2000)里,所發展的“燒水溝系列”小說。
《雨》與《猴子》既是全新系列,也有總結袁哲生之前書寫探索的意義。在《秀才的手表》全書中,最靜謐抒情的篇章“西北雨”里,袁哲生筆下的“我”,在學會說話前,“就像一臺不用插電的錄音機”,敏銳默記周遭聲響。“我”的父親“外省的”因軍職之故,每隔七天方能搭火車,從遠方回來探看“我”。他懷抱“我”,散步燒水溝。整個段落,如是形同畫卷,由一路聽聞的“我”,徐徐開展父親無聲的在場。“我”,且將父親多次回返探看,疊合為永恒一日,直至最后,當“西北雨剛剛下過”,父親死訊竟亦如一則遠方訊息,由“我”聽取。“我”開口回應,靜謐舊日隨之塌陷,燒水溝,就“再也不是從前的模樣了”。
整個“西北雨”篇章,微型展現袁哲生過往最核心的小說技藝:當不可能的觀察者“我”,以不介入之姿,縮小自己形同不存時,“我”的敘事語調縱然依舊疏離,但疏離的觀察位置,悖論地已然消失。“我”,溶入“我”所記聞的涌動景象里。“我”的人世記聞,于是帶起一種全新的感性。
同樣邏輯,《雨》開始且結束于“下雨了”這同一句子,如同落實了“西北雨”篇章中,從未實寫的雨景,且也收納父親行過的燒水溝,拓撲為更多“外省的”聚居的眷村地景。“我”在眷村里,獨自貼眼看雨。“我”,如同袁哲生小說里的許多寂寞之“我”,在淡泊中敏銳感知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仍在靜止般的蒙昧童年里,如裸命一條,如蕈菇或游魂,得以安享藏身于角落的寧靜。直到再一次,當“我”察知人世的傷逝,開口說話那刻,“我”無可挽回地,被卷入“我”已長久觀望的生命雨瀑中。
童年,在袁哲生筆下,已是人獲有生命以后的傷停補時(stoppage time),再之后重啟的時間進程,無非又是重新的苦痛。時間之傷,不因童年之“我”,對傷害一無預期,而其實,是因“我”的漫長預期,不能阻擋暴力必要再度侵臨。袁哲生建構的,深邃的反啟蒙敘事,在《猴子》里,獲得另一生命階段的檢視。在同一眷村里,那同一個“我”進入情欲萌芽的青少年時期。一方面,殘酷的暴力,被袁哲生遠隔于敘事之外,如小說中,梁羽玲如何被父親送給友人(預備養大為妻),如何返回,可能經歷如何的通過儀式,方得到同儕庇護等等細節,小說盡皆留白。另一方面,暴力卻又極其殘酷地,裸裎于那只被圈養的猴子,當定期發情時,所遭受的體罰細節中。
袁哲生以交錯焦距,支起整篇小說的繁復語境,使殘酷本質令人瞠目無言,又使暴力行徑,表露在人人日常的舉措里。在這語境中,“我”懷想一個“多么無聊而愉快的夜晚”,想著,如果能留駐時光,如永不開竅的混沌,“如果沒有陽光,這個世界多么美好”。然而,再一次,這內向早熟的心靈,只能迎向自己早有預期的失落,之后,在仍然年輕、未來猶然迢遠的彼刻,感覺自己事實上,已經“沒有更重要的事了”。小說里,日常一刻驟然重如千鈞。袁哲生筆力醇粹,而這個系列,確是他小說美學的代表豐碑。
三篇“羅漢池系列”小說,則進一步歸整袁哲生自“燒水溝系列”以來,對鄉野傳說類型寫作的持續探索。就此而言,李永平的《吉陵春秋》(1986),更明確是他借鑒的對象。袁哲生本意,不在審酌小說里,這般封閉的生活形態,是否必然只能如此封閉,別無其他出路,而是企圖以因襲生活的眾生相,示現循環時間的完成,或終結。如我們所知:在小說中,當小月娘走上母親月娘的舊路,建興仔繼承雕刻店,克昌仔奉老和尚之令剃度;當新生代完美地,填補上舊世代的位置時,傳說結構已然自足彌合。
這類對位結構所碰觸的主題,不免是人的自由意志,與人之宿命性的沖突。以希臘悲劇為例,理論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即主張:“最杰出的悲劇,反映了人類對其存在之基本性質的勇氣”。這是對自由意志的價值認納。他接著判定,悲劇的“源頭”,“是古希臘文化中認為生命脆弱、危險到令人惡心的生命觀”。他描述這群作者置身的,宛如布滿暗雷之戰區的現實世界,在其中,“虛弱的理性只能斷斷續續地穿透世界”,而“過去的包袱重重壓著現在的熱情志向,要趁它剛出生時就把它掐死”,于是人若“想要茍活,惟有在穿過生命的地雷區時小心看著腳下,并且向殘酷又善變的神明致敬,盡管祂們幾乎不值得人類尊敬,更遑論宗教崇拜”。
現世這般難測,行路如此艱險,這群作者為何還能穩確創作?為何不放棄直面那些永無答案的問題?對此,理論家小結,“或許,惟一的答案只存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抗壓性,以及將它們化為藝術的藝術性與深度”。
對比伊格頓描述的天人交戰,則我猜想,袁哲生借“羅漢池系列”所創造的最深刻懸缺,其實是諸神的隱匿。在他筆下,眾生皆低眉垂首而活,重壓他們,使他們扼殺個人熱望,放棄追求更可喜之生活的,毋寧是人世里的情感絆結。袁哲生表述了一種深情的退讓:因為不忍離異親者,人選擇認命;而總在退讓一刻,人對彼此,展現了近于神的質地。
也于是,借著擬寫一個恍如神境之倒影的人世,袁哲生依舊孤自參詳,且認納了“人生實難”的基本事實:同對此基本事實,人與人竟已無可沖突。在這倒影世界里,“一生最大的心愿便是建立道場,弘法利生”的老和尚,一生僅能暫以民宅為寺,且寺內并無佛像。而仿佛是為倒逆時程而來,贖償此缺憾,小月娘等人,終以一生絆結,粹聚成華麗絕倫的觀音像。然而,這般對個人而言,形同偶然、難再重復的粹聚,也只能湮沒于紛至沓來的時間洪流里,成為無人知曉其緣由的古物。人世終爾無傷無逝,無有索引。
這可能是作為小說家,袁哲生最復雜的善良:他對筆下人物的始終哀矜,不輕易評價,極可能是因就他看來,去敘事,去指認一段逆旅期程此事本身,不免已然預告一種論斷,無法,不指向必將壞空的時間之劫。面對人之無法改寫的共同宿命,寫作,使寫作者益發自覺渺小。這里頭,甚至可能不存在著理論家所謂的,“化為藝術的藝術性與深度”的個人超脫。袁哲生書寫,因此有其格外令人動容的反書寫征狀。
一段時日,我思量關于上述書寫技藝審酌,與倫理設想間的關聯,猜想其中的深刻豐饒,與顯在矛盾,心中于是也不無疑問。我在想,在虛構世界里,為何“作者僭越角色去發聲”此事本身,對他而言,是必不可犯的禁令?作為作者,他會不會太過謙抑?因為,以他的書寫能力,倘若這預設禁令并不存在,他會不會寫得更放松,更自得其樂?
也因以現代小說的尺度看來,明快切入角色內心,去剖析,去猜測,去提出假設并再次推翻,恐怕是作者必要犯的險。這類犯險開放的,可能會是更有效的辯證,或對話,使我們不總是將存有的幽暗,閉鎖為詩意空景。也使人的所謂“宿命性”,在我們以“小說”命名的這種文學體裁里,獲得更多面向的討論。倫理上的提問是:一位悲憫善諒之人,有無可能深涉與深解人間難免之惡?藝術上的提問則是:會不會正因為我們太過謙遜,所以我們無法在創作上跨越自我設限,再更遠行?
這類大而無當的疑問,主要還是提問給作為學徒的我自己。我寄存心中,暗自思索,從與他相處伊時,直到現在。從2004年,袁哲生離世算起,一個十年過去,第二個十年將半,對心中疑問,我沒能找到更好解答,但是,袁哲生的作品,我還是反復重讀,像是重新辨識一個坐標,或一個能靜止躁動時程的寶貴反證。這部書,因此既是一個終點,也是一個更其恒遠的起點。因袁哲生書寫,已在臺灣文學史劃下一個平寧安定的刻度,是新一代創作者,私淑與臨摹的重要文本。他的不可能隱秘的缺席,屬于這些文學從事者,共同珍重的過去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