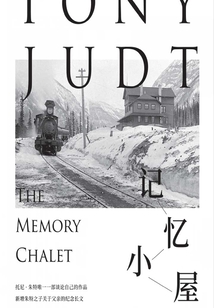
記憶小屋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駐足停留
我爸爸在2010年8月去世前,開始了一本新書的寫作。“是時候去寫那些人們理解的事情之外的事情了,”他下定決心,“去寫那些人們關(guān)心的事情同樣重要,也許還更重要。”我爸爸理解的事情是20世紀的歐洲歷史。而他關(guān)心的事情是火車,幾乎比對任何人和任何事都要關(guān)心。他新書的標題是《移動:鐵路的歷史》。
他把在倫敦帕特尼區(qū)度過的童年都花在漫無目的地乘火車游蕩上,就只是為了乘火車而已。夏天,他乘坐古色古香的郊區(qū)電力火車,周游倫敦郊區(qū)和英國起伏的山丘,然后回到克拉彭交匯站(Clapham Junction),在那里一排排呼嘯的柴油火車和宏偉的蒸汽火車慢悠悠地駛過19個不同的站臺,他從中選出回家的路線。我小時候一直聽他說起這些令人留戀的回憶,腦海中想象8歲的托尼如何端詳著黑暗而霧蒙蒙的倫敦。[1]
只要有機會,爸爸就會帶我們乘著火車環(huán)游歐洲。我們在巴黎北站(Gare du Nord)乘上蜿蜒前行的TGV高鐵,或者在布魯塞爾火車南站(Gare du Midi)乘上藍黃相間、四四方方的比利時區(qū)間車,或者在英國帕丁頓站乘上跨越隧道的歐洲之星。我們總是提前到,這樣爸爸就能在候車大廳啜飲一杯雙份意式濃縮咖啡。
就像我爸爸曾經(jīng)寫過的,如果車站是他的“大教堂”,時刻表就是他的圣經(jīng)。“我的歐洲是用火車時刻來衡量的。”他寫道。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年圣誕節(jié),媽媽送給他一本庫克的歐洲火車時刻表[2],這本書里寫滿了關(guān)于來往火車最新的細節(jié),即使是地方線路也有。這本書在他床頭柜放了好幾個月。我爸爸曾是位社會民主黨人,在大多數(shù)方面他極力倡導平等主義,他對以下事實非常受用:火車從來不等待任何人。“鐵路旅行,”他寫道,“毫無疑問屬于公共交通。”
我爸爸如此關(guān)心鐵路準時的影響,其中另一個原因是鐵路旅行顯然也是歷史的。“現(xiàn)代生活真正的不同之處,”他寫道,“不在于無牽無掛的個人,也不在于不受約束的國家,而在于個人和國家之間的存在:社會。”鐵路的出現(xiàn)標志著這一歷史轉(zhuǎn)折。乘火車成為社會集體前進的物理性體現(xiàn)——不僅跨越了地理,也跨越了時間。
這就是歷史學家托尼·朱特對火車寓意的堅定理解,也許很大程度上他帶著專業(yè)性偏見(deformation professionelle)。不過,當我閱讀他關(guān)于鐵路的文字時,最打動我的一點是他的寫作與和我朝夕相處的那個人——私下里的托尼,作為父親的托尼——之間幾乎毫無相似之處。對那個托尼來說,鐵路顯然是單一的、與歷史無關(guān)的。他最關(guān)心的兩列火車都不是關(guān)于共同前往某地的:一列在叫作繆倫(Mürren)的瑞士小鎮(zhèn),另一列在比前者稍微大一些的、叫作拉特蘭(Rutland)的佛蒙特州小鎮(zhèn)。它們在開往永恒之境的路上,在那里,過去并不要緊,歷史從不存在。
要去往繆倫,你必須乘火車。勞特布龍嫩(Lauterbrunnen)山上的冰川反射的陽光落在這個山谷小鎮(zhèn),現(xiàn)出一塊塊亮斑,從這里出發(fā)的纜車輕輕地晃動著,帶你越過懸崖來到格魯施阿爾普(Grütschalp)。一輛小巧的淡褐色單節(jié)客車從格魯施阿爾普出發(fā),沿著山坡緩緩前進,猶如一條電蛇。在把你送到繆倫之前,這列車只在溫特埃格(Winteregg)停靠,這里有一家典型的瑞士咖啡館,供應咖啡和冰淇淋。一路上你還可以看到少女峰和埃格峰令人驚嘆的風景。自1891年以來,這條火車路線就沒變過。
在前往繆倫的火車上,乘客幾乎全是游客,而且都是英國游客。我爸爸在1956年跟著他的爸爸喬(Joe)第一次到這里。喬出生在比利時,但那時他已經(jīng)是一個地道的倫敦人,操著英國中低階層的口音,把繆倫視作一次逃離:逃離他的妻子(他們最終還是離婚了),逃離倫敦,重回大陸。幾年前我問喬,關(guān)于繆倫他還記得什么時,他告訴我有一種寂靜。“那里太安靜了,就像一片寂靜的冰,這個小村莊被四周的山給淹沒了。”確實如此,50年代和今天一樣,在繆倫除了聆聽寂靜,你無事可做,只有褐色電力火車日常呼嘯而過的轟隆聲才會打破這種寂靜。那里沒有汽車(沒有路能通往山上),而且只有426名村民。繆倫的旅館——我算了一下只有7家——有將近1500個床位,但幾乎從來不會客滿,在夏天尤其如此,而我爸爸就樂意在那時候去。
作為一個20世紀50年代的孩子,我爸爸對瑞士似乎沒有受到戰(zhàn)爭影響這件事印象深刻。那里的旅館依然“到處是陳舊而堅固的木頭”,他寫道。火車是井然有序的,技術(shù)上無懈可擊,在歐洲其他地方基礎(chǔ)建設(shè)被毀壞的情況下,那里是一個幸運的意外。爸爸最喜歡引用哈里·萊姆(Harry Lime)在《第三個人》中的一段話,他在每次演講中都會偷偷塞進這段話:“在波吉亞家族統(tǒng)治意大利的30年中,他們導致了戰(zhàn)爭、恐怖、謀殺和流血事件,但他們也催生出米開朗琪羅、達·芬奇和文藝復興。在瑞士,人們擁有兄弟般的情感——他們保持了500年的民主與和平,那么這又催生出什么?布谷鳥鐘。”他覺得這是一種稱贊。
但是,當我閱讀他的著作,我很難區(qū)分爸爸小時候和成年后對繆倫的看法。當他還是個孩子時,繆倫也許能使他逃離日常學童生活的疏離,也許它意味著一個遠離倫敦的庇護所,又或者這里只是他父親熱愛的一處優(yōu)美風景。但我認為,當他開始研究20世紀的歐洲歷史,繆倫扮演了一個不同的角色。我爸爸選擇成為研究他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時代的歷史學家。他孜孜不倦地進行這項工作:他的資源庫就是他身邊的世界,始終在那里,就在他眼皮底下。我猜想,我爸爸在繆倫也許可以不像歷史學家那樣思考;沒錯,也許這里是一個象征童年懷舊思緒的基地,也是一個可以深度緩解學術(shù)壓力的地方。如果無事發(fā)生,那里就沒有可以研究的歷史。
1916年到1918年間,大約有400名英國士兵和軍官在繆倫安家。他們是戰(zhàn)時的受傷俘虜,根據(jù)英德遣送協(xié)議被扣押下來。瑞士的地理位置和中立性使其成為完美的地點: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和比利時人在這里交換俘虜,且無須冒著這些俘虜會重回戰(zhàn)場的風險。這些士兵去往繆倫的旅程和爸爸在50年代的旅程一樣,和我今天所做的旅行也一樣:先坐纜車,再乘一列慢慢前進的褐色火車。
也許意識到他們可能在瑞士逗留許久,這些士兵把這個瑞士村莊變成了一個家鄉(xiāng)的超現(xiàn)實模型——一個在阿爾卑斯山上的倫敦。1917年5月27日,他們重新命名了繆倫的幾條街道。你可以沿著“皮卡迪利大街”閑逛,走到“老肯特路”,然后再從那里一路漫步到“弓街”,你或許會在那里駐足,觀看火車從“查令十字火車站”例行出發(fā)。(“這里的地形相當復雜。”一位軍官承認。)這些被拘禁的英國人建起了商店和訓練中心,有一位木匠、一位裁縫、一個牙醫(yī)診所、一個駕駛學校,甚至還有一個鐘表商店。為了消遣,他們開設(shè)了基督教青年會(YMCA)禮堂,設(shè)立了一家擁有2000多冊英文書籍的圖書館。他們在居住的旅館外成立了運動隊——比如說埃格峰旅館隊和少女峰旅館隊比賽足球——而且仔細地記錄比賽結(jié)果。
士兵們和遠在英國的親友聯(lián)絡(luò)(經(jīng)常寫信問親友要錢),但他們很少聽到關(guān)于周遭發(fā)生的激烈戰(zhàn)事的消息。有時,他們什么消息都不想聽到。當?shù)仉s志《在繆倫被拘禁的英國人》(British Interned at Mürren)的編輯們要求倫敦的通訊記者不要發(fā)來最新的戰(zhàn)事信息,也許是為了避免引起希望或恐懼。“好幾次我們聽到重型武器發(fā)出的回聲,提醒我們過去發(fā)生的事情,”雜志編輯在第一期雜志上寫道,“最后一次,我們或多或少耐心地等待著乘纜車下山……回家的那一天。”
最終,基督教青年會的廉價煙草耗盡了,為了消磨時光,士兵們開始思考應該坐在汽車的哪個位置,纜車在運送他們飛速下山時會不會突然斷裂。“小鎮(zhèn)的一頭看起來死氣沉沉,一片荒蕪,而另一頭也沒好多少,”1917年10月,一個無精打采的作者在雜志上若有所思地寫道,“總的來說,我們孤獨又悲慘。”
當戰(zhàn)爭結(jié)束了,士兵們在繆倫創(chuàng)造的小世界也終止了。《在繆倫被拘禁的英國人》雜志悄無聲息地停刊了。村莊的道路又被重新命名。那里的旅館不再代表著不同的運動隊,重新開始接待富有的英國游客。仿佛是,僅存的一絲文明在某一天毫無征兆地從地球表面消失了。有兩年的時間,400名英國士兵焦急地盼望著坐上小小的電動火車,從“查令十字火車站”出發(fā)離開繆倫,回到現(xiàn)實世界。
2002年,爸爸第一次帶我們兄弟倆來到繆倫。我當時8歲,和他1956年第一次到這里的年紀一樣。我們乘了四班火車:從蘇黎世機場站到東因特拉肯站,乘的是完美無缺的現(xiàn)代市內(nèi)火車;從因特拉肯站到勞特布龍嫩站,乘的是一輛稍慢但同樣準時的區(qū)域火車,車上有淡藍色的聚酯纖維座位;一輛通往格魯施阿爾普站的齒輪索道纜車;最后乘坐一輛米色和淡褐色相間的電力火車來到繆倫。“依然無事可做,”之后他這樣寫我們的這次旅行,“置身天堂。”
我確信當時爸爸并不知道大約85年前被拘禁在此的士兵們會同意“無事可做”的論斷,但反對“天堂”的說法。而且,要是他知道《在繆倫被拘禁的英國人》,知道被重新命名的街道,知道旅館球隊,我覺得他會說歷史證實了他的直覺。英國士兵和我爸爸乘上同樣風景優(yōu)美的火車,同樣懷有逃離歷史的感受,但只有一方對此享受。
我媽媽、我弟弟和我在每天晚上沿著傾斜的小路走到爸爸那里。跑到山坡的比賽讓我們氣喘吁吁,山上純凈的空氣讓肺部冷卻下來,我們都沒有說話。爸爸的輪廓漸漸清晰。他像一個接球手,身形健壯結(jié)實,粗脖子,面色紅潤,獨自站在干冷的天氣里,頭上禿頂?shù)牡胤椒瓷渲妭惤譄魯U散到埃格山的光亮,埃格山黯淡的輪廓在藍黑色的天空中劃出一道難辨的影子。我望著爸爸,爸爸望著群山;一切靜止不動。在那一秒,我才知道沒有什么是不變的。
2004年,至少在比喻意義上,鐵路把我們從紐約帶到佛蒙特州的拉特蘭郡。當時也有其他理由,“9·11”事件的震動讓我們和許多其他紐約人試圖尋找一個避難所,一個飛機不會撞上魔天大樓、世界依舊沒有改變的地方。我們住的隔板房在一個山丘的頂端,離鎮(zhèn)上有20分鐘路程,屋里老舊的木頭橫梁總是嘎吱作響。在山腳下,一堵常綠植物組成的圍墻遮住了鐵路。爸爸拿著雙份意式濃縮咖啡,每天兩次站在后門廊,遠遠地看貨運火車穿過樹林。“因為有火車站,我們特意選擇拉特蘭。”媽媽說。對爸爸來說,火車意味著拉特蘭就是美國的繆倫。
拉特蘭是美國鐵路公司(Amtrak)的“伊森·艾倫”特快列車的終點站,這趟列車每天從紐約城出發(fā)。火車頭是一個巨大的內(nèi)燃機,蹲坐在車輪上,每天深夜抵達拉特蘭,每天清晨出發(fā)。火車站里唯一運行的另一輛火車是一輛驚天動地的貨運火車,在拉特蘭和馬薩諸塞州之間來回運輸丙烷、大理石和其他任何貨物。但是爸爸從來沒問過為什么這塊不大的佛蒙特州飛地(與之形成對照的比如伯靈頓或曼徹斯特這樣的大城市)能夠擁有到紐約的美鐵路線或者毗鄰我們家的貨運鐵路。
和大多數(shù)美國人相比,拉特蘭郡居民花了更多時間接受鐵路。到1840年,美國已有超過3000英里的鐵軌,但是佛蒙特州沒有一條。由于擔心趕不上經(jīng)濟繁榮的熱潮,佛蒙特州的商人們促成了一份關(guān)于從拉特蘭郡到康涅狄格河的鐵路特許狀,一個火車站赫然出現(xiàn)在小鎮(zhèn)中央。鄰近的西拉特蘭的大理石產(chǎn)業(yè)以及代理人產(chǎn)業(yè)開始繁榮起來。在1849年向拉特蘭——伯靈頓線的司庫們發(fā)表的演講中,激動的主席T.福萊特正式宣布:“佛蒙特州將完全參與到那些大企業(yè)帶來的愉快享受中,后者是當今時代的標志。”火車越多,拉特蘭就能向前走得越快。
和火車一同到來的是移民。為了逃離家鄉(xiāng)的饑荒,愛爾蘭人從波士頓和紐約啟程,參與鐵路建設(shè),最終在拉特蘭安家。瑞典人聽聞大理石采石場的工作后也來到這里。之后波蘭人也來了。然后,在世紀之交,意大利人和希臘人來了;芬蘭人、匈牙利人、捷克人也來了。拉特蘭曾是新英格蘭清教徒組成的小鎮(zhèn),1900年這里有天主教教堂和希臘東正教教堂,波蘭語和意大利語學校。拉特蘭鐵路公司在1897年的一份小冊子中自夸說拉特蘭是“新英格蘭北部最重要的市政當局之一”,這是因為拉特蘭是“本州的鐵路中心”。
但這種情形沒有持續(xù)下去。鐵路的氪石[3]——汽車,最早在1920年就入侵拉特蘭。1927年,一次由暴風雨引起的嚴重洪水對拉特蘭的鐵路橋梁造成了不可修復的破壞。1947年,又一場天災弄折了這個蹣跚產(chǎn)業(yè)的另一條腿。1961年,一次工人罷工和工廠停工給鐵路業(yè)帶來最后的致命一擊;拉特蘭鐵路公司破產(chǎn)了,拉特蘭鐵路站場徹底荒廢了。“在我看來,某種厄運似乎突然降臨在拉特蘭。”一位當?shù)厝吮г沟馈T谖业耐辏靥m的人口暴跌,當?shù)睾B逡驒M行,社區(qū)變得同質(zhì)化和衰老化,一個沃爾瑪超市建在了曾經(jīng)的鐵路站場上。
我媽媽同意我的直覺,即爸爸了解拉特蘭歷史的梗概,了解這個小鎮(zhèn)上曾有火車運行,了解這里無聲的永恒取決于曾經(jīng)存在的鐵路如今已經(jīng)消失了。他知道拉特蘭郡和繆倫并不相同,被動的美國田園牧歌式的火車和歐洲對乘火車經(jīng)歷的重視并不相同。但他在這里和在繆倫一樣,把歷史放在一旁。
2008年,爸爸的ALS病到了晚期。到2010年,他被禁錮在輪椅上,下半身已經(jīng)癱瘓。從刷牙、小便到夜晚入睡,每件事對他來說都成了嚴酷的考驗。但最糟糕的部分是他的火車歲月結(jié)束了。“我的病最讓人沮喪的事情是,”他寫道,“我意識到自己從此再也不能乘火車了。”
他希望火葬。他和媽媽考慮把骨灰撒在兩個地方:拉特蘭和繆倫。但他們擔心,我們也許會賣掉拉特蘭的房子,畢竟佛蒙特只是瑞士的次要版本。而且,爸爸已經(jīng)把他的偏好公之于眾。“我們無法選擇人生在何處啟程,卻可以選擇于何處結(jié)尾,”他寫道,“我知道我的選擇:我要乘坐那輛小火車,無所謂終點,就這樣一直坐下去。”
火車對爸爸來說是一切的解毒劑,正如他認為火車對我們也意味著如此。“如果我們失去了鐵路……我們就忘記了如何共同生活。”如果他失去了他的鐵路,他就忘記了如何獨自生活。“當然,我本應該孤獨地體驗鐵路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他曾這樣推測。
爸爸沉溺于虛構(gòu)的繆倫和虛構(gòu)的拉特蘭,如此他違反了自己最基本的準則,即我們有責任了解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的歷史。檢視它們的過去,我們會發(fā)現(xiàn)繆倫成了一處優(yōu)美的監(jiān)獄,拉特蘭成了她前身的陰影。如果這些小鎮(zhèn)及其火車沒有任何歷史,那么它們才能是永恒的。(如今懷舊之情主宰了美國大選,這可能是一個簡單但有用的提醒:拒絕承認某地的歷史會招致對此地現(xiàn)狀的錯誤觀點。)
我父親把拉特蘭和繆倫視作免疫于歷史潮流的地點,除此之外,他沒有再寫到過這兩地。這個決定不是純粹而簡單的否認,也不是一種道德矛盾。對爸爸來說,歷史是一項鑒別性的技藝,其中必須有一種值得認真對待的張力,而在現(xiàn)代歐洲的宏大圖景中,繆倫或拉特蘭看起來似乎毫無問題。“那里甚至沒有過不對勁。”他寫道。
但是,我覺得爸爸這一拒絕背后有更多的東西。他理解歷史可以多強大。檔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時所實踐的專業(yè)化歷史,以及我爸爸踐行和相信的歷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現(xiàn),既沒有清晰的歷史發(fā)展感,也沒有為迷思制造提供足夠的空間。檔案能夠擊碎懷舊之情和多數(shù)人的記憶。在顯而易見的益處之下,還有一些遺憾地不可更改的東西。我們可以修改歷史,歷史學家也常常這么做。但是撤銷歷史,收回我們知道曾經(jīng)存在的歷史,這要難得多了。
我打算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想知道我爸爸是如何發(fā)現(xiàn)了這兩個小鎮(zhèn),它們遠隔重洋,唯一的聯(lián)系就是他的所愛——火車與它們的關(guān)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本能地轉(zhuǎn)向檔案。這種本能來自我爸爸。他把他的拉特蘭和繆倫這兩個原始的迷思,留給了我。但同時他把使它們祛魅的工具也留給了我:他對歷史的熱愛,他相信檔案能幫助自己解釋這個世界的信念。我同時繼承了這些天賦,但是我忘了把它們分開保存。直到現(xiàn)在我才意識到,對我來說,通往繆倫的電力火車將喚起閑散的英國士兵的記憶,他們遠離社會,一頭栽入無聊之中。而現(xiàn)在看來,拉特蘭的貨運火車似乎伴隨痛苦的匱乏而來。當我鍵入這個句子時,這列火車就在我身后的樹林中緩緩駛過。我無法除去這個。爸爸和我知道的一樣多,而且比我走在更前面。火車并不會把我們帶入或帶出社會,歷史才會如此。
2010年8月,我們前往繆倫撒下爸爸的骨灰。在去那里的路上,我們意識到把一個人的骨灰盒留在這列電力火車里,這件事本身有點過于平庸了。把爸爸的骨灰撒在鐵軌上也不是好的選擇,我弟弟令人信服地爭辯說,爸爸不希望追求不朽的程度,和他熱愛火車的程度一樣深。
因此,我們轉(zhuǎn)而去遠足。從繆倫火車站——“查令十字火車站”——啟程,我們走到鎮(zhèn)外,走上一條覆蓋著小花和帶霜的草地的泥土小路。這條小路不斷上升最后穩(wěn)穩(wěn)地通往山上,比鐵軌高出幾百英尺。我們抵達一處連綿的草原。草原下面就是陡峭的懸崖;在一大片常綠植物中,幾處鐵軌在寒冷的陽光中閃爍可見。我們把他的骨灰撒在這里。
但我不確定我們有沒有弄對爸爸的遺愿。畢竟,他是一個歐洲人,站在你家后門廊觀看來往火車的拉特蘭模式只是一種美式妥協(xié)。他對別人沒有這種耐心,就像他小時候在英國時那個“盲目獵奇”的青少年,只是站在那里看著火車進站出站。火車作為歷史的媒介,作為現(xiàn)代性最好的部分,作為公民社會或其反面——只有在一個人成為一名乘客時,這種象征主義才有效。你不得不駐足停留。“火車的特點在于,”爸爸曾說,“你得先乘上車。”
丹尼爾·朱特
(潘夢琦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