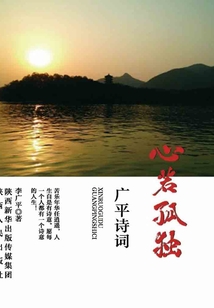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3評論第1章 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心若孤獨——廣平詩詞》
廣平初給人的感覺比較寡言,但其實他是個外冷內熱的人。他有著一份還算自由的工作,認識以后知道他很喜歡古詩詞,許是因了我也喜愛古典詩詞的緣故,我們一見如故,似乎相識多年的老友,并不陌生。
因而才知曉,近幾年他除了工作還在細心地經營著自己的另一份事業:寫詩詞。工作和詩詞將他的心房填得滿滿,他靜享其中。前段時間他邀我為他的詩集寫點東西,我欣然接受了,于是有了下面這篇《序》。
詩是什么?
竊以為:詩是安放情感的。痛苦在這里安置,歡樂也在這里安置,當我們難過或悲傷時,詩就是承載這個“痛”或“喜”的載體,在這一兩小時或更長時間里,我內心或波濤洶涌,或翻江倒海,或天地俱毀,連同看得見看不見的眼淚一起,而在他人眼中,我是一如往昔的“我”,只是添了些失落罷了;我內心或柔情無限,或春風滿園,或氣息舒暢,在別人眼里,也只得一個“喜上眉梢”而已,我們可以和詩中意象翩躚起舞甚或凌亂,卻真正難與作者一起感受,因而共鳴者何其少,知音者何難尋?也才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話。
同樣,廣平在他的詩詞里,痛著他的痛,傷著他的傷,快樂著他的快樂,有人欣賞也好,無人閱讀也罷,自顧自地寫著,自顧自地活在他這一片繽紛里,就像“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里的木末芙蓉花——王維《辛夷塢》,怎能不說他這又是另一種生命狀態,紛紛開且落,我自繽紛我自落,無需青山感傷懷。
廣平的痛在“天涯此去作清歡,竹馬青梅,封入詩箋”里——廣平填詞《一剪梅》;廣平的殤在遠處“二十年來心飄零,何處是歸程”里——填詞《虞美人》;循著明月終南下,廣平“對酒當歌解愁容,只是無緣醉此生”——填詞《蝶戀花》。
他在詩詞里安放好他的情感,抖落情海灰塵與哀傷,去掉眼底寂寞,提筆化劍走向另一個精神高地……
詩是拉近人與人心里距離的。
我們每個人在世間行走,卻可在詩的方寸間接近,我可以不與你皮相五官相識,卻可在靈魂里與你相遇片刻,雖不深刻,但也懂得,那短短的幾行字,有你飄著雪花的人生,秋日的私語。
于是,在那一刻,你我與作者心靈接近。
廣平把這幾行小字交與你,有緣,便讀懂它,讀懂他,它就真真筆墨生香;無緣,它仍只是幾個字,鉛印墨塊,則白白與你相見一回。
但是也無妨,晚照秋山時,飛鳥棲來處,廣平是一定要“不知棟里云,去作人間雨”的(王維《文杏館》),他雖言痛收筆墨,不再寫詩,然,他仍是“詩能言盡心中意,待到濃時賦新詞”——《詩詞戀》。
他既不愿作“棟里云”,便會化作“人間雨”,會適時地又一次拾筆,呈出他生命中的純凈,那時,必是過濾掉更多的雜質的純凈,如他做《志愿者》般的純凈,如他《悼志愿者劉娟君》的執著。
他怎會不與你再次相見?
詩是另一種虔誠的信仰。
有人說小說使人深刻,散文使人明理,詩使人聰慧,聰慧與否我不清楚,抑或,膚淺的聰慧便是“淫巧”了?我倒更想說,詩是另一種虔誠的信仰。我們仰視它,信賴它,同樣,它也根植于廣平的心中,卻又高于他的心,它長于廣平的心,卻又不沾染廣平的俗務,對于每個喜歡詩的人來說,皆與此同,像虔誠的信徒,無論皈依與否“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
廣平“而今不學御溝上,春風不再傷離別”,他不但做慈善,做志愿者,還把骨子里的豪情櫻花般綻放,他贊祖國瑰麗江山,填詞《浪淘沙》;他深懷家國情懷,就有了《抗戰》《詠杜甫》。
我們不必太去注意他的平仄工整與否,如果深陷其中,則是一種精神破費,我們只留意他飽滿的、圓潤的情感,他把他的喜怒哀樂全然寄托于五言、七言里,我們跟著他體味人生的五味。就像《紅樓夢》里,黛玉對香菱論詩一樣:“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文學是使人精神,視野開闊的,而不是越讀人生面越狹窄,所以才有寬闊的空間去容納人間的風雨蕭索。
是啊,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他用虔誠的心守護著那方凈土,那片赤誠,那隅神圣。
我已經與另一個靈魂在詩香瓣里相遇,碰撞,那么你呢?
打開它,它會走入你心;閱讀它,它會給你訝異。
丹馨
2017年11月
丹馨,原名田麗娜,陜西散文學會創聯部副主任,長安作協理事,詩歌委員會副主任。